玩一场用“协议”讲故事的中局游戏 | 系列访谈三 · Venkatesh Rao(下)
The Summer of Protocols (SoP) is a seasonal research program that supports the study of protocols in and across fields. In late 2022,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which helps maintain the core blockchain protocol of the same name, commissioned the program in order to broad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rotocols and how to manage them.
GCC 作为 SoP 的共同主办方将在华语区同 Uncommons 一起,额外支持用华语写作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从 2024 年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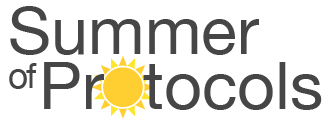
也许学完所有课程的学员会收到一个协议学位(Protocol Diploma)。这很有趣。
◽ SoP 的前两年就像一盘国际象棋的开局(opening)。顶尖棋手对开局了如指掌,也能轻松驾驭棋子所剩无几的残局(end-game)。但今年,我们进入了复杂的中局(mid-game)。
◽ 讲故事的天赋(talent for storytelling)和写作的天赋(talent for writing)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能。LLM 可以弥补这一点。
◽ 我们举办的科幻小说比赛收到了 55 份作品。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在培养一种新的“读写能力”(literacy)。就像学习一门语言或一种游戏,你需要掌握它的语法和规则。“协议”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语言。
◽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让全世界更多人掌握“协议思维”这门通用语言。它像音乐或情感一样,可以跨越文化。无论是在中国与 GCC 社区合作的伙伴,还是北美的研究者,当我们讨论协议时,我们谈论的是关于人类行为和共享理念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说着同一种语言。
◽ 我希望能看到,就像曾有过“西化”和“美化”一样(它们有好有坏),未来也能有“中国化”(Sinification)。我希望十年后,当别人问我时,我可以说:“嘿,我在某些方面被‘中国化’了。”但我感觉,似乎存在一种犹豫。
*本文为 Venkatesh Rao 访谈(下):玩一场用“协议”讲故事的中局游戏。访谈上篇请参阅邮箱过往邮件。
受访者
Venkatesh Rao is a writer and consultant based in Seattle. His current writing can be found on the the Contraptions newsletter. Since 2023, he has been the program director of the Summer of Protocols program. Between 2007-24, he used to write a popular blog called Ribbonfarm (now archived). He is the author of Tempo (2011), a book on timing and decision-making; and The Clockless Clock(in progress), which is being serialized in his newsletter.
访谈人:7k, 技术与媒介研究者,前实习记者。关注货币史与加密货币行业,密码朋克文化。
编辑:方庭
Summer of Protocols 的过去时态与进行时态
7k: 请向读者们介绍一下 Summer of Protocols 今年的进展。
Venkatesh:这已经是 SoP 的第三年了。第一年很轻松,我们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在一张白纸上探索,所以充满了乐趣。第二年,我们开始尝试将初步的研究想法付诸应用。而到了第三年,我们正试图应对更复杂的挑战,同时在三个核心领域展开工作。
方向一:教学 —— 重新思考教育的契机
我们正从“研究”走向“应用”,现在则希望尝试“教学”。因此,教学(Teaching)成为了一条主线。今年的核心项目之一就是“课程开发资助”(Curriculum Development Grant)。这背后当然有一个有趣的背景:美国的大学体系正因与政府的资金争夺战以及人工智能等诸多因素的冲击而备受压力。常言道,危中有机。正因为学术界困难重重,现在或许正是重新思考教育的绝佳时机。
这个项目进展还不错。我们在 Edge Esmeralda 举办了一场静修(retreat),其中有很多都是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成员,比如上海纽约大学的 Helena 还有北外的一鸽。不过,我们真正能看到产出,要等到秋季,这些老师在秋季学期会完成完成他们的课程,并在一个线上学校进行试讲。最终的成果将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否真的有用。
方向二:场景营造 —— 科幻小说定义新类型
第二个方向,我们称之为“场景营造”(Scene Making),其中一个核心工具就是“协议科幻小说”(Protocol Science Fiction)。
过去两年,我们的 Newsletter 更多是发布活动信息和项目细节。今年,我们有意识地决定赋予这份通讯更大的使命——将它转变为一本线上科幻杂志(我们通过 Substack 发布),专门邀请人们基于“协议”的理念创作科幻故事。
这是一个有趣的赌注:当所有作家都对 LLM 感到恐慌并抵制使用时,我们反其道而行,鼓励大家积极拥抱它,用任何想用的工具来创作。我们不仅希望看到好故事,更希望作者能在文末附上创作过程的记录,比如他们是如何使用提示词(prompting)的。这部分进展得非常好,我们举办的比赛收到了许多优秀作品。作家陈楸帆(Stanley Chen)也正帮助我们从哲学层面思考,共同定义“协议科幻”这一新兴类型。
通过科幻小说和相关工作坊,我们每周都能看到新的作品诞生,Newsletter 的订阅量也翻了一番。我们发现,LLM 极大地拓宽了创作者的边界,许多有好想法但写作能力稍弱的人因此获得了表达的机会。
方向三:研究与工作坊 —— 将理论带入真实世界
第三个方向则是研究。我们在曼谷举办了一个关于分布式 AI 与加密技术的工作坊。一个重要的不一样的点是,我们利用 Sora 等视频生成工具,将工作坊的讨论内容制作成了短片并在线发布。
通常工作坊的问题在于,参与者在现场激情澎湃地头脑风暴,但活动结束后很难产生任何具体、可分享的成果。但 AI 工具改变了这一点,它能捕捉所有非正式的讨论并将其转化为可见的成果。我们制作的短片在后来的活动中反响热烈,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我们举办工作坊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从第一年的一场,到第二年的三场,再到今年已经举办的多场活动,还有为大型企业(如一家保险公司和洛杉矶水务局)举办的定制工作坊。
整个历程是从理论研究起步,进行一些应用探索,再加入科幻小说这类有趣的元素。但真正让理论变得厚重、有现实意义(gives it stakes)的,是当你尝试用它去影响真实世界的具体领域时。
此外,我们最近还启动了“特别兴趣小组”(Special Interest Groups),以在线讨论组的形式,深入探讨协议的数学基础、记忆协议等前沿研究课题。
第三年:中局的挑战 Mid Game
总体而言这三个方向都进展顺利。在那些可以反复实践的领域,我们学得很快;而在那些本身节奏就慢的领域,我们的学习曲线也相应平缓。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常对我的同事 Timber 说,SoP 的前两年就像一盘国际象棋的开局(opening)。顶尖棋手对开局了如指掌,也能轻松驾驭棋子所剩无几的残局(end-game)。但今年,我们进入了复杂的中局(mid-game)。你不能再简单地用“砸钱”的方式——比如提供一笔资助或雇佣某个人——来指望问题自行解决。现在,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度的管理和战略思考,例如:如何向特定行业阐释我们的理念?如何用科幻小说来驱动研究议程?这些都是更难的问题。
7k: 有挑战的可能才是那些必须要做的事。你提到了大概有三个主要部分:研究、应用,还有场景营造(same making),我认为这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新的,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Summer of Protocols 更多是关于研究,更多是关于人们做研究。所以你能否给我们更多一些案例,比如你提到的教育和教授们正在开发的课程;以及关于场景营造(thing making),关于那些科幻小说和那些用提示词创作科幻故事的事。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兴趣或印象深刻的?能和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吗?
课程开发的“黑客松”:“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Venkatesh Rao: 首先关于课程开发。是这群受资助者(cohort grantees)。他们正在开发非常不同的课程。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教授在做关于物联网(IoT)的协议,属于工程领域。Helena 在上海纽约大学做的更多是关于城市主义、社会学的东西。普林斯顿的 Andrés 做的是类似协议媒体(protocol media)的东西,有点像用社交网络协议进行设计,诸如此类。
它们在纸面上看起来都非常不同。但有趣的是,在 Edge Esmeralda 的工作坊上,我们让他们以“短跑冲刺”的方式快速开发课程雏形然后互相反馈。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各自为战,没想到结果是他们之间不仅找到了大量的共同点,还积极地互相借鉴想法,整个场面就像一个“课程开发黑客松”(hackathon for developing courses)。
这也催生了一个新想法:在秋季举办一个免费的线上学校,让所有人都来教授一个 90 分钟的精简版课程。虽然他们的完整课程会分散在各自的大学里,但当我们把这些精华部分汇集在一起,你就能清晰地看到不同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物联网的协议、建筑学的协议、加密领域的协议……一幅“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图景便浮现出来。完成所有课程的学员,或许还能获得一份“协议学位”(protocol diploma),这会很有趣。
讲故事的天赋与写作天赋是两回事
7k: 谢谢。那关于“场景营造”的科幻小说呢?
Venkatesh Rao: 我们的成果都发布在 Protocolized 这份 newsletter 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 15 篇科幻短篇了,非常值得一读。
这个过程最有趣的发现是:讲故事的天赋(talent for storytelling)和写作的天赋(talent for writing)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能。 很多人擅长通过电影、口述甚至舞蹈来表达故事,但写作能力稍弱;另一些人则文笔很好,却不知如何构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而 LLM 正好能弥合这一差距,它将更多人带到了这两种能力的交集点上。如果你擅长写作但拙于叙事,可以请 LLM 帮你构思情节;反之,如果你点子很多但文笔不佳,可以让它帮你把想法填充成文。它极大地拓宽了创作的可能。
人们使用 LLM 的创造力也让我感到惊讶。比如,在一次工作坊里,我尝试的技巧是“我写一句,AI写一句”,交替进行。另一些人则会用不同的 AI 工具组合,来分别完成宏观构思和文本生成。那些拥抱 AI 的人,总能自然而然地想出无数种创新的用法。
这也揭示了这项技术的独特之处:它不像一把刀或一台电脑,无论你怎么想,它的行为都由物理定律决定。LLM 更像一个人类伙伴,它会根据你的输入给予相应的回应。你越是开放、有创意地与它互动,得到的回应就越有创造力。我认为,我们正走在用 LLM 辅助写作实验的最前沿。
我们举办的科幻小说比赛收到了 55 份作品。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在培养一种新的“读写能力”(literacy)。就像学习一门语言或一种游戏,你需要掌握它的语法和规则。“协议”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语言。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让全世界更多人掌握“协议思维”这门通用语言。它像音乐或情感一样,可以跨越文化。无论是在中国与 GCC 社区合作的伙伴,还是北美的研究者,当我们讨论协议时,我们谈论的是关于人类行为和共享理念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说着同一种语言。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场景营造”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及一个围绕这门语言形成的社区。
始终在正确的剧本上
7k: 如果您要重新设计第一年和第二年的 SoP——您在之前的访谈中对它们都相当满意——您会怎么做?有什么会改变的地方吗?
Venkatesh Rao: 我想我不会改变什么。我认为我们采用了正确的剧本(playbook),并且效果很好,它基本上验证了我们关于如何做的假设。我们做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很多项目在运行时,往往试图一次性找到完美的公式,然后就停止思考,年复一年地重复它。而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第一年的正确做法,不会是第二年的正确做法。
每一年,我们都会回顾并自问:“到目前为止我们学到了什么?这又该如何塑造下一年?”这其中也包含了很多机遇主义的成分。比如,第一年我们的项目非常单一,所有研究员都在一个轨道上,方庭也是其中之一。但当我们开始第二年时,她联系到我,向我介绍了 GCC。这让我们很兴奋,觉得或许可以运行两个轨道,这能让我们获得在完全不同的地理区域运营多轨道项目的经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思考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今年,我们正式设立了东南亚和北美两个轨道。如果一切顺利,明年我们希望能增设一个南美轨道。再往后,我们希望实现完全的去中心化,让所有轨道都成为平等的同行。目前,我负责的主轨道更像是“高级轨道”(senior track),而其他轨道,比如 GCC 和东南亚轨道,则像是“初级轨道”(junior tracks)。明年,我们希望看到其他项目也能成熟起来,成为真正的对等伙伴(P2P, peer-to-peer),因为这能让整个生态系统更健壮。
所以,我不会改变过去的做法,重要的是不断从已有的经验中学习,并对新的机会保持开放。我总是在设计中留有余地,如果有趣的想法或机会出现,我们就能抓住它们,做一些即兴和创新的事。这是我思考方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柔软的“生态系统式管理”
7k: 过去三年既是 SoP 的旅程,也是您个人的旅程。对您个人而言,SoP 最有价值或最独特的方面是什么?
Venkatesh Rao: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 SoP 之前,我从 2011 年起做了 12 年的独立咨询顾问,基本上是独自工作,客户都是些公司高管,我和他们一对一合作。但在那之前,我在施乐公司时曾管理过团队。我当时是经理,带一个大约 10 到 12 人的团队,一个标准的 Web2 软件工程团队。那时我才三十七八岁。现在我 50 岁了,在时隔十多年后,又重新回到了管理岗位,并且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管理。
我学到最多的是,这是一种非常柔软、轻触式的“生态系统式管理”(ecosystem style of management)。它不像管理一个大学的学术部门或公司的某个部门,那种管理是从带 10 个人到 30 人,再到 100人、500 人,是同一种管理模式的规模扩张。而在这里,你更像一个催化剂(catalyst),身处一个由数百人组成的网络中。SoP 网络里有大约 70 位校友,还有很多人为我们的出版物写作。但我和 Timber 管理的并不是一个“组织”,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而更像是催化、是对生态的某种监护(stewardship)。这是一种非常有趣且困难的管理方式,我们都在共同学习,也收获颇丰。回过头看,这是一段非常棒的学习旅程,我现在成了一位“生态系统催化剂”式的管理者。
7k: 这也是一种新的说法。
Venkatesh Rao: 对我来说是新事物,因为我是个老家伙(old guy),学的是老方法,必须先忘掉坏习惯才能学习新东西。但对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未来唯一会了解的管理方式。他们现在毕业,进入的是一个已经去中心化、P2P、线上化的世界。他们将不会再接触到老式的工业化管理。他们必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他们会比我这样的人准备得更充分。
SoP 在华语世界:在文化上,能等来更普世的“Sinification”吗?
7k: 最后一个问题:您对 SoP 在中国的发展有何期待?或者说,您想对中国的观众说些什么?
Venkatesh Rao: 我认为,不仅是中国(PRC),而是全世界的华人社区,作为一种文明,你们需要做得更多。你们已经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大量的制造业、科技研发都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不是美国、苏联或大英帝国那种老式的超级大国。从历史上看,中国几千年来都非常内向。在其文化巅峰时期,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蛮夷。即便是现在,中国也非常庞大,一个人可以花一辈子只思考中国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拥有一种真正的世界意识和更普世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这正在发生,比如在工业、科技和地缘政治层面。西方现在很恐慌中国在非洲建设基础设施,但我认为这和西方在 19 世纪所做的事情并无不同,重要的是要用更智慧、更人道的方式去做。
但还有文化层面。西方在过去 500 年里,创造了启蒙运动、开放的自由文化、科学方法和普世主义等哲学。它创造了一种可供输出的世界观,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被“西化”了——我来自印度,你在中国,但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被西化了。这显示了一种强大文明世界观的力量。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有所犹豫。它更内向,喜欢在中国境内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华文明。我希望能看到,就像曾有过“西化”和“美化”一样(它们有好有坏),未来也能有“中国化”(Sinification)。我希望十年后,当别人问我时,我可以说:“嘿,我在某些方面被‘中国化’了。”但我感觉,似乎存在一种犹豫,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不敢去说:“嘿,中国确实有一些东西可以普世地教给世界,而世界会为此说声谢谢。”
我认为这正在以一些微小的方式发生,比如遍布全球的唐人街,它们带来了美食等美好的文化。但我希望看到更大层面的东西,比如在教育等领域。我希望看到一个非常普世、智慧、积极的全球视野出现在华人世界。像 GCC 这样的团体就是一个有趣的开端。
7k: 除此之外,您对 SoP 在中国的发展有何具体期待?因为今年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
Venkatesh Rao: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中国的参与者们自己来决定和引领。我们只是帮助它启动,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催化剂。第一年,我们有几位华人背景的参与者,由我来指导。第二年,GCC 轨道变得更独立,Fangting 在策划项目和做出版物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今年则更加独立。
这就是我所说的要变得更全球化和更具领导力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作为超级大国,而是要从跟随到引领。为什么应该由我来告诉中国的 SoP 轨道该做什么?应该是中国的 SoP 轨道来告诉我该做什么。 领导力应该从那里涌现。像 Fangting、Stanley(陈楸帆)、Helena 还有 Amber 这样的人才很多,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现在,我希望能看到更多领导性的想法从那里产生。事实上,一些最激动人心的科幻小说正来自华人世界,这已经是一个领导力的例子了。所以明年,我希望能看到中国的 SoP 轨道承担起领导角色,比如组织一场活动,邀请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参加,从跟随到引领。
系列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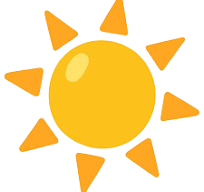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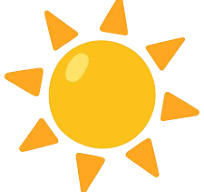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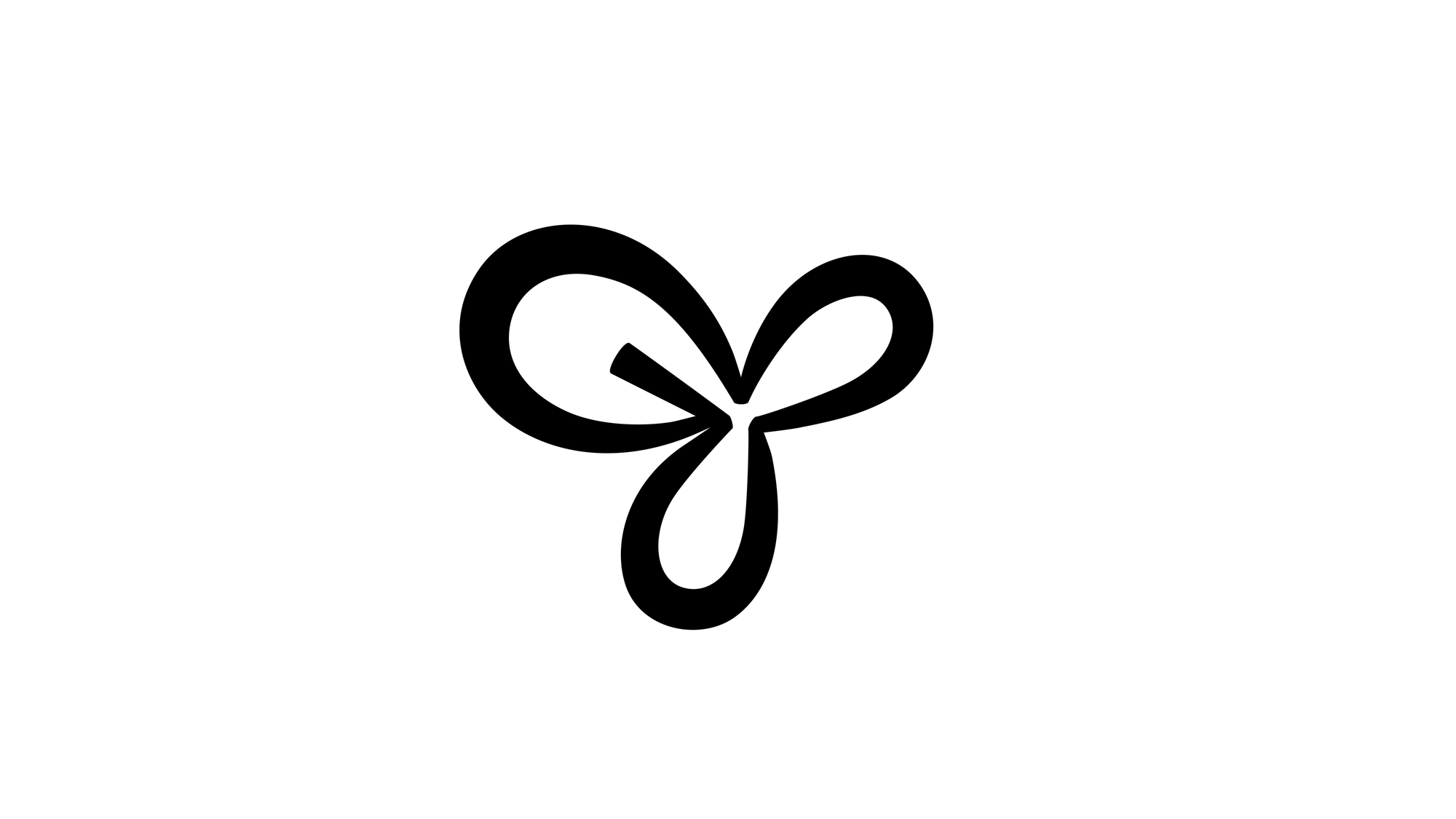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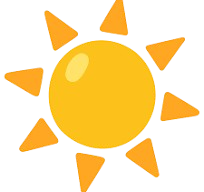





Discu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