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天世界终结:技术与社会的协同秩序 | 系列访谈一 · 王一鸽
The Summer of Protocols (SoP) is a seasonal research program that supports the study of protocols in and across fields. In late 2022,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which helps maintain the core blockchain protocol of the same name, commissioned the program in order to broad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rotocols and how to manage them.
GCC 作为 SoP 的共同主办方将在华语区同 Uncommons 一起,额外支持用华语写作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从 2024 年开始)。
现有秩序的广厦将倾,而在漫长的瓦解过程中,我们仍然有时间重新组织对自身的叙述线索。
导语
在 21 世纪生活成为了一种想象力训练。起初这种想象是实验室式的,是学科容器中的被命名为科技哲学或社会学的袖珍沙盒推演;但很快,容器被打破,我们走入真实世界:“无法想象”就意味着无法理解。
于是我们开始不断述说一个技术脱轨的世界:科技行业内与外的人重复预判人工智能跑步进入具身智能时代,再跑步进入到每个人身边;加密货币终于成为了硅碳通用货币;语料库逐渐被人类所不能理解的陌生语言占满……
旧秩序的冰块在融化,技术环境的温度上升似乎和气候变暖一样,不可拒绝。
在所有不能接受的世界末日中,最不能被接受的或许是最后一种:语言的陌生。秩序的终结总是并非来自于可以理解的毁灭方式,而是来自于不能理解的方式。语料库之内是现有秩序的积灰,语料外是未被垦荒的新现象,也是尚未形成的秩序的源头。真正的想象使用的新语言正来自于此。
这不是科技行业内部的工作,这是人文学科的工作。人文学科的 funding 正在日益减少。最顶尖的学校裁撤终身职位,其他学校无法支付起门可罗雀的纯人文研究院系,年轻的学生有些正被告知“这些都不是非学不可的东西”。如果人类共享同一张“重要-紧急四象限”的 to-do list,那么“人文学科”这个长期处于“重要不紧急”象限的事,就被一拖再拖、一划再划,直到我们确实不再能够使用一种足够精确的语言去描述,“What the hell just happened?”
真正应该肩负起支持人文学科责任的或许有一天会是科技行业。作为制造 “the hell just happened” 的行业,我们知道,尽力去“理解”要比其他事情的优先项更高。
我们放飞了一只只风筝,直到它飞得过高,看不清楚(我们已经放出了这样的风筝)。风筝不见、隐入太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与它们的关联、失去了理解它们的语言,也一并失去了在风向中判断方向的能力,线也就真的断在空中。
在当今,我们需要如何对人文学界给予支持?
2025 年,这个问题作为帮助形成捐助理念的问题之一,也将停留在我们的视野。在秩序崩解的二零年代,我们将发起一系列以「如果有天世界终结」为主题的科技人文访谈,去轻盈地一起探索:假如(这个)世界终结,我们还要怎么重新叙述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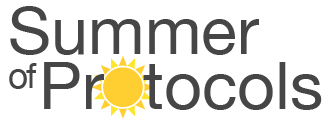
◽ 如果要送给多年之后的人们一幅画,你会送给哪一年的人,怎么画这幅画?
◽ 当今的人文学界主要依靠政府机构的捐赠,长远来看,科技行业的捐赠有可能改变人文学科的生存结构及其资源来源吗?短期来看呢?
◽ 如果要写一本书,书中是你一直最想写、最感兴趣的话题,你有无限的时间进行研究(包括任何技术或概念),你会选择哪一个课题?
◽ crypto 这门技术最让你 surprise 的地方在哪里?
◽ crypto 的最核心价值之一被称作是独立性,即独立于任何现行政经体制之外,不靠边站、也依然能够让人进行协作进而生存下去。你同意吗?如果同意,需要哪些必备条件?如果不同意,你认为它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什么?
◽ 只针对自己的专业领域,你理想中的“数字公共物品捐赠基金”捐赠优先级会是什么样的?
◽ 在所有不能接受的秩序崩坏/世界末日中,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种?
受访者
王一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硕,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 政治社会学、经济史与量化史学研究、城乡与发展社会学
所授课程 本科课程:社会学导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 研究生课程:美国不平等与社会分层
序:一幅给未来技术时代的静物画
当技术可以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类的身体包括心智时,我们政治秩序中关于人之为人的基本假定是不是会被突破?我们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方庭:从一个画面开始——如果要送给很多年之后的人们一幅画,你会送给哪一年的人,怎么画这幅画?
王一鸽:我以前做的很多东西其实总涉及一些历史的部分,相应也有一些沉重感在其中。我最近在读福山 02 年的时候写的一本书,《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聊 post human 的问题。之前我没有看过这个书,最近因为指导本科生写论文,讨论到 AI 相关的话题时,聊到后人类的这个分析视角。福山的这本书,核心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在 02 年那会儿就已经在关注生物技术、基因技术这类技术对未来的影响。
让我很有触动的是他在书里提出了很多关于"什么是人"的思考,包括当我们在探讨人性的基本构成这样的问题时,其实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生物学基础,而他关心当技术可以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类的身体包括心智时,将会对我们理解什么是人和所谓“人性”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在科幻电影或作品里也经常被讨论。比如说,如果基因可以被选择,如果人类拥有了类似上帝的能力可以制造"更好"的人类,那我们政治秩序中关于人之为人的基本假定是不是会被突破?我们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20 世纪的历史,从两次大战到纳粹、共产主义集权,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灾难。德国乐队 Rammstein 有一个有争议的 MV Deutschland,它用一个黑人女性来象征德意志,讲述德国历史中那些复杂纠缠的部分。MV 里有一个场景,几个乐队成员演绎了纳粹时期的画面:一排戴着绞索的犹太人,穿着条纹囚服,胸前都带着集中营给"不合格人类"的身份标志。
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决定制造出"更优秀基因"的人,我很想把这样一幅画送给他们,提醒他们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
方庭:看来这是一幅 warning 的画。提醒那时候的人,仍然是有一些伦理边界不能够跨越的?
王一鸽:对的。我们在走向一个可能,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技术,可以进行所谓的自我优化或者是更新时,它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我觉得这幅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20 世纪给了我们两种方式去警示,一个是 《1984》 的警示,然后另外一种我觉得可能就是《美丽新世界》的警示。
我最近都在看生物技术这一块,因为我觉得AI也可能会加速生物技术发展,包括 Web3 community 讲的 DeSci 还有 longevity 等等都涉及到生物技术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读福山的那本书还挺有意思的,他讨论的是在所谓生物层面上的变化之外,从社会或政治的层面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更有挑战性的议题。
长远来看,科技行业的捐赠有可能改变人文学科的生存结构及其仰仗的资源来源吗?
这套系统的运作到最后会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逻辑,它让一些当下的声音无法发出或者难以被听到,从而失去很重要的时效性和即时的反应,但一旦当它们进入所谓历史的范畴后,又更方便被权力所辖制或删改。
方庭:我想到有一种朋克类型叫做 Biopunk,生物朋克。其他类型的朋克,cyberpunk, cypherpunk, solar punk 或者 lunar punk,都有相应的比较稳定的和技术共生的图景,但是生物朋克被称为最恶心的一种朋克,在视觉表现上会有很让人不适的画面。它们的视觉呈现本身也是一种 warning。Alife 领域也有一些对“湿人工生命”(wet Alife)的探讨,不过我们可以先到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关: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乱七八糟风雨动荡的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人文学界仍然主要依靠捐赠维系,在美国依靠不稳定的特朗普政府,在中国也依靠主要是官方力量。其中来自科技行业的捐赠占比很少,来自 crypto 和 AI 这种新兴行业的更少。长远来看,科技行业的捐赠有可能改变人文学科的生存结构及其仰仗的资源来源吗?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王一鸽:人文学界依赖政府经费这件事有很多很明显的 limitation。前两天在"知识分子"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自然科学、理工科发展的文章,讨论国家战略和研究者个人兴趣的平衡问题。那篇文章写得挺激进的,甚至有点迎合;但在人文这边,"服务于国家战略"已经变成了大家不得不去承受的方式。
从 80 年代到大概十年前,情况都没有今天这么严重。我听到过一些国内企业会给高校的老师和研究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后来有些企业因为经营出问题或其他原因而中断了。在国内产权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很难分清到底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还有一些民间基金会,但在整体环境下空间被压缩得很严重。可能这几年科技领域在国内才开始有人考虑这个问题,之前这方面都很少讨论。
但我觉得,如果说科技的本质是要围绕人和人的需求,那么所有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应该是非常核心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不过比较遗憾,在这方面看到的案例还是不太多。更常见的是传统的方式,比如捐助一些社会福利或慈善性质的活动,深入讨论技术人文的事情确实不多。
在香港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文学者主要靠写书写文章维生。但在大陆,审查制度一旦收紧,这些空间也被压缩得很严重。这让我想到做博士论文时读那些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版业的研究。当时启蒙思想家面临的问题其实和今天一样,伏尔泰、卢梭这些人的作品,也因为审查制度的存在,常常实际上是和地下出版商的盗版书籍一起流通的。有些启蒙思想家的书,外面可能是一个书皮,里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内容,甚至书皮可能是色情的、暴力的。这很像我小时候八九十年代的记忆,那时候只要听说是禁书,不管因为什么被禁,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去看。本来未必相关的内容却被审查制度而归入一类。
其实晚清和民国时期,很多人除了服务于政府,还可以通过出版、办报来获得收入。但现在的出版管控,还是会影响部分人文研究的传播和生存空间,主流体系可能与商业领域不同,但也会存在缺乏透明性和原创保护不明晰的问题,学界的例子并不算少,实际是在压榨一些没有被很好保护到的青年研究者群体,包括我自己也有过一些经历。这套系统的运作到最后会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逻辑,它让一些当下的声音无法发出或者难以被听到,从而失去很重要的时效性和即时的反应,但一旦当它们进入所谓历史的范畴后,又更方便被权力所辖制或删改,总之是个很系统性的问题。
方庭:我感到上面我们聊到的更多是科技对学术的 infra 层面的改变,比如经费和出版制度,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事情;那么相对在更短的时间框架中,科技行业的资金进来之后会有哪些即时性的效用呢?每个人都会想要捐助和维护他关心的东西、relevant 的事情,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同时保证相关性 relevance 与被捐助者的创作自由?
王一鸽:我首先想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曾经有人质疑过部分医药类的研究会存在一些和医药公司的绑定关系,里面的那个 scandal 挺多的。但我认为如果有良好机制的保障,利益相关、包括自主性的释放并不必然让它影响到科学研究本身的中立性。人文学科在议题上相对模糊一些,很多讨论会涉及到一些价值性的东西,它可能会是更开放和多元的,但因此也更需要一些公共机制来保证这一点。我们可以邀请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来参与创作和讨论,甚至促成可能的对话或交流,这也是帮助形成一个 public sphere 本身。
你会把无限的研究时间锚定在哪一个技术或概念上?
我们往往假设系统的变动是逐步的、可预测的,并遵循稳定的因果关系。
方庭:谢谢。下一个问题会更个人化一些,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假如由你来写一本书,书中是你一直最想写、最感兴趣的话题,你有无限的时间进行研究(包括任何技术或概念),你会选择哪一个课题?
王一鸽:虽然我不知道这里假设的“无限的时间”对我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但总的来说我最感兴趣的应该是复杂系统相关的内容。
就像我们第一次电话的时候聊到的,还有刚刚聊福山的书对生物技术变革的影响,或者是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当前我们对于变化的理解,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制度、规则或协议的层面,仍然深受线性思维的影响。我们往往假设系统的变动是逐步的、可预测的,并遵循稳定的因果关系。这种认知模式也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于诸如自由、平等和市场机制等核心原则的理解。即便是博弈论这样强调互动关系的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也常常停留在简化的二维模型,比如人们更经常援引的也是 two by two (囚徒困境),其实往往很难去设想更高维度、多因素交互的非线性动力过程。
这种线性逻辑带来了很多挑战。比如它使人们往往低估了系统中非线性反馈机制所带来的影响,现在的两极分化问题,就表现尤为突出。财富、权力或信息的快速积累往往遵循的是一种正反馈的强化机制,大家现在会说比如“强者恒强”、“赢家通吃”,然后就导致power law式的分布和结构性不均。但是自然系统中常常通过负反馈机制实现对系统波动的抑制,使得变量趋于平均态,呈现normal distribution或回归均衡。这种差异的存在说明,在思考和理解社会复杂性方面,我们需要有意识引入非线性视角。
其实社会中的大量现象都是体现高度非线性特征的,最近大语言模型火了让大家在现实中也理解了什么是 emergence,涌现,但还有很多现象,也都很难用线性模型去解释的,比如制度变迁里面的路径依赖问题、社会思潮或者意识形态的转变也经常像是突变、社会运动或秩序维系中也存在着某些临界点行为,等等,理解它们需要去考虑系统中那些复杂交互和反馈的动态关系。只有借助非线性,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均衡如何达成、意识是什么、情感是什么、以及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这些问题。
在面对人工智能和未来技术的挑战下,"人之为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会被重新提出。现在我们确信人类是有一些特质的,这些特质要求我们承认作为人的完整性 —— 也就是只要这个个体是作为人,ta就应该得到最基本的被视为人的尊重。这种信念构成了现代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基础。这种观念在现代以前可能源于神学或自然法,认为人具有某种“来自上帝”或“自然秩序”的神圣性,但现在,尤其是在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将“自然”解构为一系列偶然性与选择,而不再是某种目的论秩序,很多研究持续对人类行为做出机制性的解释,这种背景下,有关人的特殊性的这种信念的基础其实在面临松动。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本能地坚持,在谈到"人"的时候会有一种可能不一定是用“神圣性”去表述——某种特殊性吧,就像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类关涉人类最基本尊严的核心价值——也有人可能说这来自自由意志,但现在自然科学比如认知神经科学家也可能认为自由意志也许也是幻觉——anyway,这件事在我这里觉得恰恰是很好玩的,就是涉及到某些很基础的困难,反而让我看到通往复杂系统视角的可能性。
因为我理解复杂系统之所以复杂,意思就是它具有一种整体性,就是涌现性,它是没办法通过对个体的简单还原论来理解的那个层面。而我觉得这种非线性意义上的复杂系统的整体性,可能恰好就跟构成了我们理解那种奠定“人”之基本权利和尊严的某种底层逻辑,某种基础价值紧密相关:它不是来自于个体属性的总和,而来自于系统性协同中的某种不可简化的结构性。
理解这一点可能帮助我们超越将 AI 仅仅简化为强化学习算法或计算能力演化的理解思路。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政治动物,他假设人类具有的政治能力,不仅仅指涉参与治理的能力,而应该是涉及到情感判断、语言行为、意识系统协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不是某种姑且称之为“社会性意识”的涌现结果呢?能不能认为它与潜意识、符号系统乃至制度性结构交织而形成了我们称之为“人”的某种整体性呢?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会想在这个方向进一步探索,比如人之所以为人,是否正是因为其意识和行为模式处于某种复杂系统的涌现节点,以及这个系统是否具有某种形式的结构性平衡与非还原的价值基础?这是个很开放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向,但对我一直都很有吸引力。
方庭:可以告诉我你之前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是什么吗?
王一鸽:"Printing a road to revolution"。我讨论的主要是晚清时期的印刷技术如何带来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媒体市场或思想市场,进而影响到20 世纪初的社会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为第一次民主化进程。因为我的导师是经济学家,所以研究方法还是比较注重传统的计量经济学等严格的方法论。
这个议题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所谓的文科生问题了。当然这个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在西方传统中,文科精英多是法律专业出身,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十年,这些法律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到前辈们能找到的那些工作岗位。这被认为是理解当时社会思潮和政治秩序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罗伯斯庇尔这些人都是学法律的。
在中国因为有科举制度,读书人传统上主要研习儒家典籍。但是道光之后,通过科举晋升的机会在收窄。很多学者讨论过,科举承诺给这些文科精英(可以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的位置越来越少。比如 1856 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直没能考公上岸的基层知识分子。
到了 1890 年前后,一些改良派,包括康有为这些人,开始接受新思想。这得益于道光年间开始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办报纸。虽然规模不大但持续时间很长。康有为这些传统儒生接受新思想,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思想和报刊出版。他们不仅接受西学思潮,同时也学习这种实践方式,自己开始办报刊。
清政府直到 1908年才出台《大清报律》,但即便如此它也没有能力进行像今天这样的审查制度。所以当时不少传统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办刊物。
研究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既涉及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问题,也涉及对现代政治本质的理解。有个研究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的学者 Lawrence Stone 说,英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词语的革命"(wordy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在中国这场革命中也有类似之处:当时蓬勃的社会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通过翻译等方式创造出的新词语本身就很重要。
现在想把这篇论文改写成更有可读性的书,因为原文有大量技术性的内容,比如地图表格和统计数据等等,另外社会网络分析这部分当时写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跟复杂系统这方面也相关,希望这部分能够扩展。
Crypto 最让你 surprise 的地方在哪里?
方庭:谢谢,下面可能会转到与 crypto 本身相关的问题。作为一个之前也接触过加密技术的人,crypto 最让你 surprise 的地方在哪里?
王一鸽:那还要从零几年讲起。那时我在北大准备申请美国读书,正赶上08金融危机。印象很深刻,因为北美的老师回复说他们系的预算被砍掉了2/3,只能勉强维持本系学生的名额。
后来 2010 年我去了香港,记得有次跟一个北大力学系毕业、在科大读 ECE 的朋友吃饭。她提到有个教授要给研究生付钱,想用比特币支付。我们在食堂聊天时觉得挺有意思,还在说"要不要搞一点(比特币)",但最后也没付诸行动。那时比特币的涨幅跟后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当时虽然没读过中本聪的论文,但觉得白皮书的这个理念很有必要。对当时国内来说,美国 07、08 金融危机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跟着发了 4 万亿。虽然对华尔街的玩法不太了解,但因为 4 万亿的原因,很多人都去买黄金。在这个背景下比特币出现,用人工方式去锚定、应对货币超发的问题,大家觉得很 fancy。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这类畅销书在国内读者很多,感觉整个社会对货币问题有很多兴趣和讨论。
最让人惊讶的当然是它发展得特别快。我记得 2014 或 2015 年在微博看到一个帖子,用摩尔定律预测到 2020 年左右通用人工智能会出现,画出了现在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曲线。那个帖子带着焦虑感在说,技术发展速度会完全超出想象。我还转发并问过 CS 的学生怎么看,他们也表示有很多担忧,但觉得无法阻止。
但最让人惊讶又最不让人惊讶的是,它真的按照预测的速率在加速发展。它不以人的意志、恐慌或忧虑为转移,就是这么快。
方庭:大家常觉得这种变化会比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长得多,但实实际上可能5年、10年就突然指数增长了。
王一鸽:是的,我们的思维常常是线性的,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往往不是。
中立的 crypto 技术,会成为最终区别于国别体系的第三方力量吗?
方庭:对的,速度确实是 Crypto 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我们继续聊 crypto 的下一个问题,不过这次是价值层面。有一些人认为 crypto 最大的价值是让个体“不用选边站”,现在你可以理论上可以不选中、不选美,可以通过自足的一套具有刚性 hardness 的政经体制,一个微观的体制去协作、去生存。你同意这个观点吗,如果同意的话,要最终发展成这种独立中立力量,需要哪些条件?如果不同意,为什么?
王一鸽:我在情感上是非常同意的,或者说我非常希望它确实是这样。这也是最初看到去中心化时让我感动的地方,它像是承诺了一种甜蜜的自由。自由对于某些人来说它确实构成了最高的价值,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当然去中心化虽然可以更好地保证独立性,但如果要谈及效率,这就是它需要面对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些不同的协作方式或新的合作机制。
虽然我觉得自由很重要,但最近我有点悲观的观察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自由这件事(还)没那么重要。这让我怀疑Crypto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是多数人的选择,还是始终会是少数人的选择。
最近一次让我有点震动的经历是和一个年轻的女性主义者聊天。她是个青年研究者,来自中产家庭,聚焦性别和技术这样的前沿议题,打算去国外深造。但她恰恰认为在家庭关系中,依赖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要全然独立。当然这可能也涉及到情感的维度在不同个体这里的理解和实践。我相信她的理由是基于她的处境和思考。
这让我意识到,在社交媒体或大众话语里,你听到更多的不是"fight"或按照自己想法去活,而是一种"和解"或"surrender"的态度。绝大多数人采取的姿态可能不是像 Crypto 这样,选择通过自我定义和创造去为未来的共同体做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时,我能感觉到它的复杂性和其中的沉重。回看 20 世纪的历史,我们当然相信技术进步——其实我相信但凡对技术有某种信仰的人,他们都不可能是全然拒斥某种 progressive 的立场的;但也需要面对一些左派实践中通常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怎么让那些更愿意选择依赖性生活方式的人理解 Crypto 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参与的可能?这可能不是必备条件,但值得多想。
方庭:听下来主要其实还是是否愿意给予信任的问题,在你刚举的例子中,对方愿意去相信,“依赖”就代表他相信那个体制不会完全抛下他不管。但是 Crypto 就是一个主张去信任化的、一个非常零度的一个体制,他就是。其实我觉得它最温暖的地方在于他全都是最恶意的假设,就是他假设只要有第三方,那第三方在某个拉长的时间框架内,几乎一定会作恶。
王一鸽:对,这让我想起对我影响特别大的电影《国家的敌人》。我中学时看的,讲述一个人在美国偶然发现重要秘密后被 FBI 还是 CIA 追杀的故事。记得有个场景,他被堵住所有道路后换了辆自行车逃跑。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对权力的不信任可能也和家庭有关,老一辈在政治运动中被冲击的经历让人对权力比较警惕。特别在中国这样的社会, 20 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里,权力会不断用各种方式把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一茬茬收割掉,留下来的文化是选择妥协和合作的。这对 Crypto 在中国来说无疑是个挑战。
在美国反而很有意思。美国个人主义虽然有其神话性,但确实是其文化核心。但近期的政治变化显示,不只是传统认为的红州白人男性在支持 Trump,还包括 Hispanic、African American 和女性。这反映出后工业化、信息为核心的时代,整个经济和社会逻辑都在改变。
如果 Crypto 要继续发展去中心化理念和对个体自由的保障,就需要更准确地把握当下社会运作机制。从 70-80 年代开始,information 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很多底层逻辑都在改变。我在给学生讲社会分层与流动时,很多学生提出传统的职业体系划分、收入分配方式似乎和今天不太一样了。他们看到更多的是网红等新形式,完全不同于二战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运作方式。
所以今年 Summer of Protocols 这个"accelerating order"主题很重要,到底是什么在被 accelerate?当我们在说 order 的时候, order 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是核心的问题。
对应专业领域的模拟捐赠设计
方庭:这恰好也某种程度上牵涉了下一个问题——去加速什么,去肯定什么,去放大什么。GCC 是一个捐赠基金,Uncommons 也在辅助它进行 SoP 捐赠的运营。捐赠的对象涉及到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也牵涉到排序和优先级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来设计一个你专业领域中的“数字公共物品捐赠基金”,仅仅站在自己专业的立场,你会希望它的捐赠优先级是什么样的?
王一鸽: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应该是最难的一个,因为毕竟我对背景不够了解,不清楚 stakeholder 具体指向谁。不过我可以先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
我去香港之前,在北京参加过一个性别和性少数群体相关的草根 NGO。当时我们承接了一个项目,是关于中国反家暴法的。这个法律出台前,经过了很多妇女专家十几二十年的努力。中国法学会有个反家暴网络,汇集了法学、性别等领域的专家。我们要调查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中的亲密关系暴力、原生家庭暴力等问题。因为我有这个学科背景,就去做志愿者,帮忙写报告。
后来我去了香港,那时候奖学金还不错,我就和另外几个朋友商量说,可以做个小基金,每年给对性别研究感兴趣的人两三千块钱,支持他们做实地研究。我们组建了 committee,找了两类人:一类是有专业训练和学科视角的,另一类是了解社群的。
这两类人之间需要平衡。有时从学科角度觉得某个研究容易出成果,但社群的人会指出问题,比如研究者可能只是把议题当作客观研究对象,缺乏主体性。现在想想真可惜,当时没把这些讨论记录下来。
我们做了两三年后,发现最理想的情况是社群的人来研究自己,并且具备研究能力。后来这个项目停了,但机构用其他方式继续运营,增加了很多活动和设计。
我觉得这反映出一种阶段性:开始可能是通过捐赠邀请外部学者,但慢慢地,一些学者会留在社群里成为核心,有些则离开。机制也从单纯的邀请变成"邀请+培育",考虑怎么鼓励外部新人加入。
虽然确实需要更多信息和思考,但我觉得可以考虑不同阶段的需求。在初创阶段可能是一种模式,但作为设计者,可能要考虑到未来的变化,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内部的人做研究,同时邀请外部伙伴对话、开会、办活动或出刊物都很好,既有核心又能扩展边界。关键是怎么在机制设计中保证核心成员的重要位置,又能开放一些位置给年度性的邀请成员。这有点像公司董事会或大学校董会,都有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具体的比例设计会涉及很多细节问题。总的来说,就像公司董事会有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大学校董会也是这样,有内部的,有外部的,还有一些重要 stakeholder 的代表。关键是怎么设计这些 position 的比例,以及参与和决策机制的设计这就会涉及到很多具体问题。
在所有不能接受的世界末日中,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种?
Death is an illusion. 没有终结,因此就没有一个“不可接受的”终结。
方庭:非常感谢。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问一个动荡的问题——在所有不能接受的世界末日中,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种?你最希望的是哪一种?
这个问题可能我的回答要让你有点失望,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世界末日这一说,在我的价值观里面,Death is an illusion ——就是我觉得死亡是一种幻象,我觉得现在我们语言通常所言的 end 其实都不会是真正的、永远的结束。就是如果说这个世界有生成的那一刻,那它生成过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世界真的有末日吗?可能就是某一些剧烈的、大规模的毁灭了,但其实一定又都会有新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方庭:这也和你之前对复杂系统的偏爱是连续的。这个回答我其实也赞成。
王一鸽:是的,我脑子里没有一个电影画面或者意义终结。当然这个世界末日如果只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的,比如说人类觉得不能接受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无数种可能性。但我想了想,我确实没有想到一个最不能接受的方式。可能有很多方式。他们是平行的、平等的,都可以去体验生灭。没有终结,因此就没有一个“不可接受的”终结。
感谢 GCC 对 Summer of Protocols 的支持。阅读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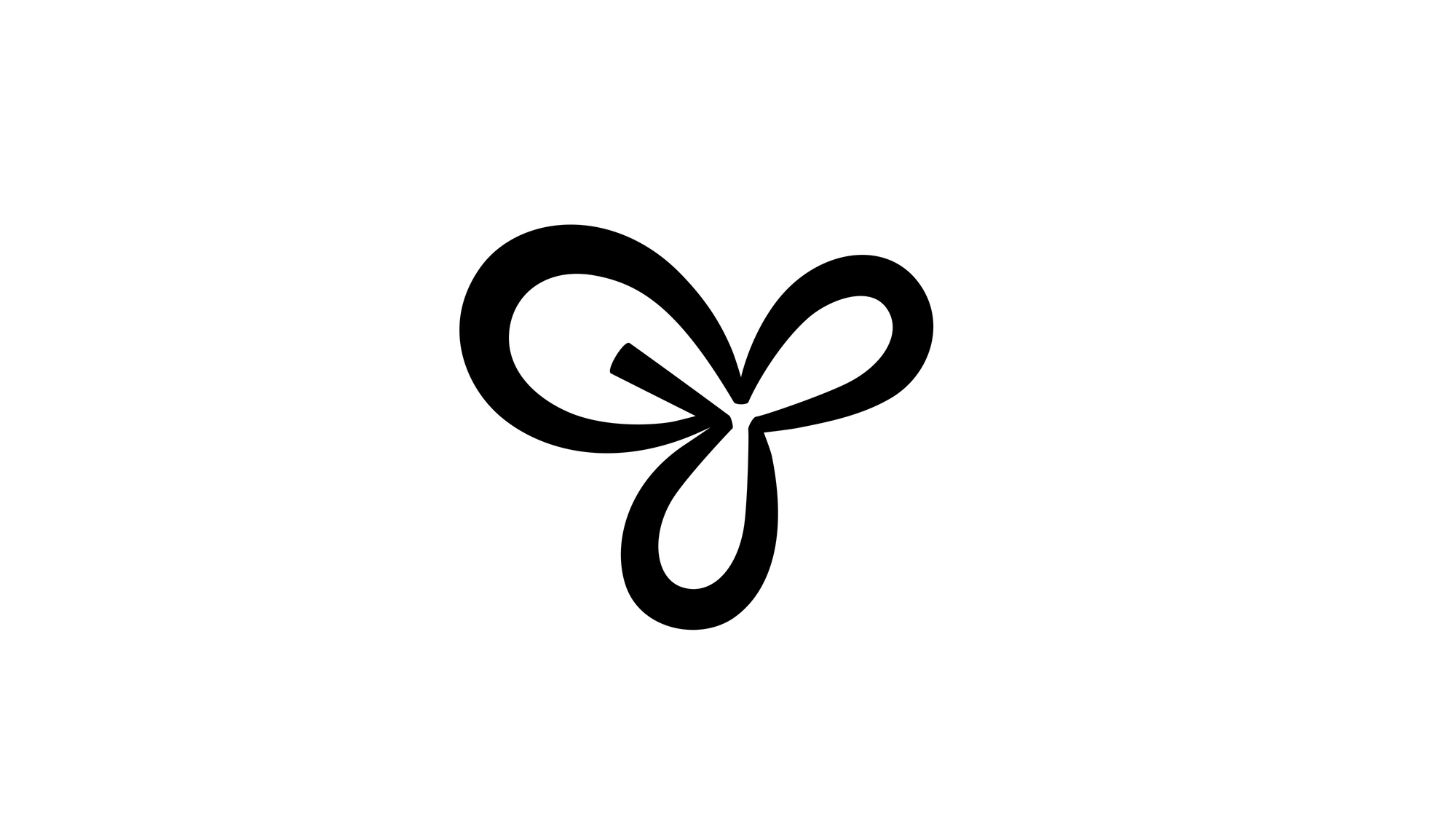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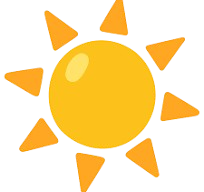



Discu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