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崩坏时代,创造一门“共同演化”的第二语言 | 系列访谈三 · Venkatesh Rao(上)
The Summer of Protocols (SoP) is a seasonal research program that supports the study of protocols in and across fields. In late 2022,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which helps maintain the core blockchain protocol of the same name, commissioned the program in order to broad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rotocols and how to manage them.
GCC 作为 SoP 的共同主办方将在华语区同 Uncommons 一起,额外支持用华语写作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从 2024 年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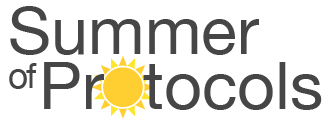
现在的问题是,基本上没有答案。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他们说:“等着一切崩溃吧,然后我们像野人一样生活在后崩溃时代。”我认为这是一种失败主义,是放弃。人类比那更聪明。
◽ Venkatesh 如何从工程学博士转型为著名科技文化作者,又如何进入加密世界?
◽ “协议”代表了社会中一种日益增长的、永久性的后台自动化水平。这些系统永不关闭,持续在后台运行,它们是智能的,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做决策。
◽ “握手”是一个抽象模式——两个实体建立连接和信任并开始互动的方式——它有自身的演化史。它是一个协议“物种”,过去很原始,但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 控制论为何会被描述成一个“基本失败”的领域?它的教训是什么?
◽ 当事物崩溃时,你要么加速崩溃,要么缓慢衰退。要保持增长和健康,必须要向系统注入信息和智慧,一旦停止它就会开始瓦解。问题在于工业时代的机构和治理模式太慢、太僵化。你必须快速行动,像初创公司一样快……但如果你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快速行动,得到的就是加速的混乱(Accelerating Chaos)。
◽ 我们不希望人们说完全一样的、同质化的语言,我们不想创造一个单一的、庞大的领域,把社会学、建筑学、工程学都合并成一个系。不,我们希望他们留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同时将“协议”作为一种第二语言来学习。
*本文为 Venkatesh Rao 访谈(上):崩坏、加速秩序与协议作为一门“语言”。访谈下篇如已订阅 Uncommons 邮件,请于一日后查收。
受访者
Venkatesh Rao is a writer and consultant based in Seattle. His current writing can be found on the the Contraptions newsletter. Since 2023, he has been the program director of the Summer of Protocols program. Between 2007-24, he used to write a popular blog called Ribbonfarm (now archived). He is the author of Tempo (2011), a book on timing and decision-making; and The Clockless Clock(in progress), which is being serialized in his newsletter.
访谈人:7k, 技术与媒介研究者,前实习记者。关注货币史与加密货币行业,密码朋克文化。
编辑:方庭
在 OG 时代如何跳上加密的船
7k: 在进入到 Summer of Protocols 的问题之前,能否分享一些您的个人背景?您是如何进入以太坊社区的?又为何对区块链感兴趣?毕竟,在区块链出现之前,您就已经在写博客了,那还是 Web2 的时代。
Venkatesh Rao: 我年纪不小了。我的背景是航空航天工程,2004 年拿到的博士学位,距今已经 20 多年了。就像我说的,我的专业背景是航空航天控制工程,一个非常传统的工程领域。后来我去了施乐公司(Xerox),在那里接触到了 Web2 的研究。我意识到印刷行业已经老旧,是个死胡同,我应该做点新东西。于是我开始研究网络技术,并在某个时候开了自己的博客。博客成功后,我以此为基础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在接触加密货币之前,我做了很多关于分布式计算、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s)的研究,这些领域都和我们现在谈论的东西高度相关。我其实很早就听说了比特币,大概是在 2009 年,一些朋友开始涉足。我自己则是在 2013 年左右入场,买了一些以太坊,所以算是个很早的小规模投资者。
但直到 2017 年左右,第一次加密货币热潮来临时,我才真正认真起来。当然,一旦钱变得多了,所有人都会突然变得更严肃,对吧?在那之前,我只是觉得“哦,我投了点小钱,不在乎它会怎么样”,后来才惊呼“哇,这可是正经钱了,我最好多关注一下”。
我曾通过博客组织过一个名为“Refactor Camp”的会议。2018 年,我们在奥斯汀将“加密”设为会议主题。当时很多对我的博客感兴趣的读者聚集在一起,帮我举办了那场会议。现在在以太坊基金会(EF)工作的 Tim Beiko,当时也来参加了。那时他正在犹豫是投身 AI 还是加密领域。参加了那次会议后,他觉得加密更有趣,于是选择了这个方向。几年后,当他在以太坊基金会负责协议支持工作时,他联系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思考以太坊的未来。那时我还在科技行业做常规的咨询工作(现在也还在继续),同时也在玩一些 Web3 的东西,比如做些 NFT,摆弄 ERC-20 代币。那是在 2019 年底,我只是在瞎玩。
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和 Tim 开始了对话。我们的交流变得越来越认真,到 2022 年,我为以太坊基金会做了一些咨询工作,这最终演变成了 Summer of Protocols 项目。所以 2023 年是第一个完整的项目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7k: 所以你在 Tim Beiko 进入 Web3 领域之前就认识他了?
Venkatesh Rao: 是的,他曾是我的博客读者。我知道他,因为他有时会发表评论,我们偶尔也会在 Twitter 上互动,就是那种程度的联系。但我们真正开始认真交谈,是在我刚开始玩 NFT 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个 NFT,他买了下来。那时我才注意到他。后来,因为我的主业是组织和管理咨询,他最初其实是想就以太坊的管理问题向我寻求咨询支持。但聊着聊着,我们开始想,或许我们应该做一个更有雄心的事,从更宏大的视角来思考“协议”。
工程与人文的融合本能:“I just got old doing this”
7k: 您自己出身于工程学背景,但却选择在哲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写作和工作,涉足 Web2 和 Web3。这种跨学科研究是如何在您身上发生的?作为一名跨学科研究者,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Venkatesh Rao: 我天生就是跨学科的。我在航空航天工程领域的专业是控制理论,本身就是工程学中最跨学科的科目之一。在我的博士期间,我也不仅限于控制理论,还借鉴了人工智能和运筹学的思想。随着我在职业生涯中日渐成熟,我思考的“画布”也变得越来越大,在某个时刻,开始写作关于人文和社科话题的文章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不会说我是突然决定离开工程学去做社会科学的。
这始终是我的本能模式。只不过随着年龄和责任的增长,画布变大了。以前我可能只是一名学生,做不了太多事,现在在 Summer of Protocols,可以对 30 个不同的人产生一些影响——他们比我聪明得多,也年轻得多,但我可以稍微“推动”(nudge)他们一下。所以,画布变得更大了,对吧?这基本上是我正常思维和工作方式的一种延伸。我只是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变老了而已(I just got old doing this)。
协议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论证(an engineered argument)
7k: Summer of Protocols 以“协议”为研究和书写核心。很多与“协议”相关的概念,都与开源、P2P 技术,甚至与 60 年代的控制论(cybernetics)或工业革命时期的自动化等术语有所重叠。它似乎都曾试图在多个学科中创造某个源于技术领域的共同语言。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协议”在今天显得如此独特,与 P2P、开源或控制论这些过往的概念有何不同?
Venkatesh Rao: 我会说,它增加了一层“共同演化”(co-evolutionary)的复杂性。现代意义上的协议,真正开始兴起是在 1970 年代末的互联网时代。如果你去查 Google Trends,“protocol”这个词的热度在 80 年代开始起飞,在 2000 年左右达到顶峰,那时所有人都在谈论互联网协议。之后有所回落并趋于平稳,直到 2017 年左右,因为加密货币的兴起,它又开始回升。
在英语世界的影视作品中,你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 80、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无论是在警匪剧还是悬疑片里,角色们都在频繁地谈论“协议”。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因为协议代表了社会中一种日益增长的、永久性的后台自动化水平。这些系统永不关闭,持续在后台运行,它们是智能的,使用计算机,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做决策。
所以,“协议化”(protocalization)不同于老式的工业自动化,也不同于更偏向结构性的“去中心化”。它更加关注行为和过程。我们对协议的定义也在不断迭代,其中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定义是:协议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论证(an engineered argument)。
想象一下,当你我意见不合时,有一些预设的规则来指导我们如何解决分歧。协议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它允许持不同意见的人达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我们越来越依赖机器来帮助我们解决这类分歧,这是全新的。
7k: 但当谈论协议时,很多人都会用“握手”这个例子来反驳我,因为在机器出现之前很久,协议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了。
Venkatesh Rao: 是的,我们经常用“握手”这个例子。它是一个经典的入门案例。在工作坊里,我甚至会让新成员们互相握手,并分析这个过程。但思考一下,这个古老的模式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
现在,计算机之间也会“握手”,TCP/IP 就是两台计算机的电子握手协议。飞机在空中如何协调?也是通过握手协议。当你不断增加复杂性和“活性”(liveness),你会发现“握手”这个模式出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并以更强大的方式被使用。比如今天你叫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你就在使用大量的握手协议:你用 App 请求车辆(第一次握手),服务平台找到一辆车并分配任务(第二次握手),车来了你用手机解锁上车(第三次握手)。
一旦你理解了“握手”是一个抽象模式——两个实体建立连接和信任并开始互动的方式——你就会意识到它有一段演化史。它是一个协议“物种”,过去很原始,但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再比如“洗手”。几千年前,人们只用水洗手,他们对细菌和感染知之甚少,但会用一些迷信来促成这件事。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李斯特和巴斯德等人意识到细菌致病,并提出必须用肥皂洗手。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医院里洗手能显著降低死亡率。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手部消毒”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医疗协议。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各种版本的消毒方式,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现在真的知道如何正确洗手了。一百年前,很多外科手术本身很成功,但病人却因为医生不洗手而死于感染,现在这种情况几乎降到了零。
很快,你还会看到 AI 和电子消毒设备被加入进来。所以,是的,协议很古老,但它也非常新,因为它是一种不断演化的技术。就像轮子,它古老到可以追溯至石器时代,但当你为高速着陆的航天飞机或在零下 180 度的火星上行驶的探测车设计轮子时,你必须用极其复杂的方式重新设计它。一个工程理念的古老,并不意味着它停止了演化。协议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控制论为何会失败?
7k: 这非常有趣。就我个人而言,当我想到“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上一次互联网技术浪潮中的关键词时,总觉得它过于“固化”(settled)。控制论系统不像是一个演化过程,即便从技术上讲,它有第二波浪潮、有反馈回路等等,但“协议”似乎天生就是为了演化而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Venkatesh Rao: 我可以多说一点。我在航空航天工程领域的专业是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控制理论可以说是工程学的原始版本,后来才被社会科学家借鉴并发展成了控制论。像诺伯特 · 维纳(Norbert Wiener)这样的控制论先驱,他们实际上都来自控制理论领域。控制理论本身历史悠久,大约有200年历史,最早的现代控制设备是蒸汽机调速器。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域,并且仍在持续发展。
然而,控制论,我个人会将其描述为一个基本失败的领域。我曾短暂地对它感兴趣,但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如果逼我一下,我就会开始滔滔不绝地吐槽它。它里面有一些好想法,但我觉得他们太早地变得过于雄心勃勃和傲慢了。控制论的问题在于,他们构建了非常宏大但不确定的系统模型,却不知道如何实际测量其中的变量,无法让模型建立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同时,他们的建模技术也不够成熟,没有真正好的计算机。最终,它变成了一种非常“空谈”(hand-wavy)的东西,我甚至觉得它近乎一种邪教(cult)。
在我看来,控制论后来被工程学以外的、带有某种邪教色彩的团体和学科所接纳。当然,我不想说得太苛刻,它确实有一些好想法,也带来了一些宝贵的教训。在很多方面,我们现在用协议所做的事情,正是在重新审视控制论曾感兴趣的那些问题,但我们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们——吸取其教训,并带来新的洞见。
那么,教训是什么?其一,我认为控制论不够实证。他们会看着一个大城市说:“嘿,我们来写一些微分方程,模拟交通、供水和人口”,然后试图在70年代的计算机上运行这个大模型,结果只会产生一堆胡说八道。
而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同。我们从“我们能实际测量什么?”开始,自下而上地构建传感器网络和回路,收集大数据,然后或许可以用 LLM 来训练模型。我们非常谨慎,从数据出发,再逐步建立模型。我们从非常小的事情开始,比如握手和洗手。我们会问:“如果要追踪疾病传播,我们该如何测量?用的是什么肥皂?它能杀死多少细菌?人们如何握手?”我们试图以一种非常微观、自下而上的方式建模。而典型的控制论方法则是宏大叙事:“嘿,让我们建一个大模型,假设每天有多少人握手,再对细菌和疾病传播做一堆假设……”最终你只会得到一个毫无用处的、充满噪音的模型。
我们试图更加实证,也采取了更偏向工程学的路径。我们不把协议看作是抽象描述事物的模型,而是看作是需要设计成系统的东西。我们直接审视现实世界中已有的协议版本,并直接在真实世界中对其进行改进,而不是创建一个过度抽象的模型,在玩具案例上做理论研究。所以,是的,我们可以从控制论中学到很多,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做得比它好得多。
“加速秩序”(Accelerating Order)意味着什么?
7k: 这也算为那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由于时间有限,让我们回到 Summer of Protocols。今年 SoP 的主题是“加速秩序”(Accelerating Order),能否谈谈它的含义?
Venkatesh Rao: 好的。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背景是,传统的全球地缘政治体系正在崩溃。二战后建立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全球化、多边条约、联合国——那种各国聚在一起,本着合作精神进行谈判和对话的时代正在远去。
过去三十年里,世界各国的孤立主义情绪越来越重,变得更具竞争性和攻击性。与此同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在下降,政府能力在萎缩,而私营部门在扩张。从悲观的角度看,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崩溃,因为人们停止了明智地治理世界和进行合作的努力。
当事物崩溃时,你要么加速崩溃,要么缓慢衰退。因为要保持增长和健康,你需要向系统注入信息和智慧。如果你停止这样做,它就会开始瓦解。问题在于,工业时代的机构和治理模式太慢、太僵化,无法跟上人工智能、加密技术等最新科技的发展,也无法应对气候变化等快速变化的挑战。这意味着你必须快速行动,像初创公司一样快。
但如果你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快速行动,得到的就是加速的混乱(Accelerating Chaos)——就像 Facebook 曾说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你跑得很快,但秩序和结构却在瓦解。所以,我们面临几种失败模式:要么什么都不做,任其崩溃;要么互相攻击,把一切烧光。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就是后两种情况。
“加速秩序”(Accelerating Order)这个想法的核心是:我们能否使用协议作为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语言,来构建既能快速行动,又能维持秩序的基础设施和系统?
这很有意义,因为通常你无法两者兼得。你要么追求速度,允许一些东西被打破;要么维持秩序,但必须放慢脚步。这是两种还算不错的选择。而“加速秩序”是我们追求的宏大愿景:如果我们能真正学会围绕协议来设计一个世界,我们或许可以两者兼得——既拥有不断增长的秩序,又能拥有不断加速的节奏。这就是我们的愿景,至于如何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等待世界崩溃是一种放弃,人类比那更聪明
7k: 我能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尖锐一点吗?当您提到“加速的混乱”(Accelerating Chaos)时,我能否将其与 Web3 中的无政府主义或市场无政府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因为您知道,Web3 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是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
Venkatesh Rao: 是的,在比特币世界尤其如此。用一句话来概括比特币世界的某些哲学就是:比特币在等待世界崩溃。 他们希望在世界崩溃后的无政府状态中,成为运行世界的新系统,成为“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式的全球治理体系。这就是比特币至上主义者(Bitcoin maxi)的哲学。
以太坊世界则不同。以太坊世界不希望世界崩溃。如果现有的机构运行良好,它不希望它们崩溃。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运行得很好,对吧?空中交通系统运转正常,我们知道如何运营电网、供应清洁水、管理医院。这些都是好东西,你为什么要毫无必要地去批评它们,并期盼它们崩溃呢?我觉得那些说“看,所有医院都是老旧的工业时代产物,我们应该推倒它们,然后每个人都自己做实验、自己制药”的人很愚蠢,而很多极端分子就是这么做的。
我认为,以太坊世界的哲学更像是:我们如何保留工业时代社会组织方式中好的部分,丢掉那些明显不再奏效的部分,然后用区块链、AI 等技术,以更具表现力、更先进的方式来取代它们?
这就是 Vitalik 称之为“d/acc”(decentralized and democratic, differential defensive acceleration)之类的东西。它探讨的是:我们能否两者兼得?为什么非要像比特币世界的人那样期盼崩溃呢?我们能否加速我们想要的部分,同时保留那些有价值的部分,并让它们变得更好?我认为,Vitalik 的“d/acc”是“加速秩序”哲学的一个版本,但不是唯一的版本。“加速秩序”是一个宏大的设计空间,我们希望在这里展开对话,探讨如何才能同时拥有“加速”和“秩序”。希望未来能有很多好的答案涌现。
现在的问题是,基本上没有答案。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他们说:“等着一切崩溃吧,然后我们像野人一样生活在后崩溃时代。”我认为这是一种失败主义,是放弃。人类比那更聪明。
“协议”能成为所有人的第二语言吗?
7k: SoP 的特点是聚集了跨学科的研究者,这一点您刚才也提到了。到目前为止,这种跨学科合作效果如何?您提到他们会互相交流,但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吗?他们真的在沟通吗?
Venkatesh Rao: 如果你去看我们已经完成的研究,你会看到很多跨领域连接的证据。事实上,我们是有意为之的。第一年,我们有一个“核心研究员”小组,同时还有“附属研究员”,他们的目标就是基于核心研究进行拓展。我们明确地设计了这种机制,并在后续几年里不断创造促进思想交叉授粉(cross-pollination)的机制。我认为效果很好。
他们不必说同一种语言,但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共同兴趣和理解,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这才是目标。我们不希望他们说完全一样的、同质化的语言,我们不想创造一个单一的、庞大的领域,把社会学、建筑学、工程学都合并成一个系。不,我们希望他们留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同时将“协议”作为一种第二语言来学习。
你可以这样想:如果“协议”能成为所有人的第二语言,那就太棒了。就像现在你我用英语交谈,英语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第二语言。协议也可以成为很多思考领域的第二语言。只要人们能进行好的对话,并将想法带回自己的学科领域去做些事情,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希望将协议作为一种第二语言、一种读写能力,像一根线一样穿插在现有学科中。
我们不强求物联网工程师和人类学家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协议,但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进行一场精彩的对话,并互相学习。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做到了。
系列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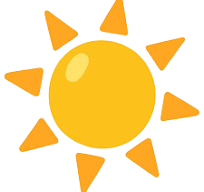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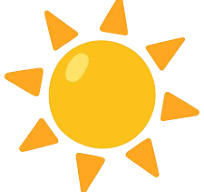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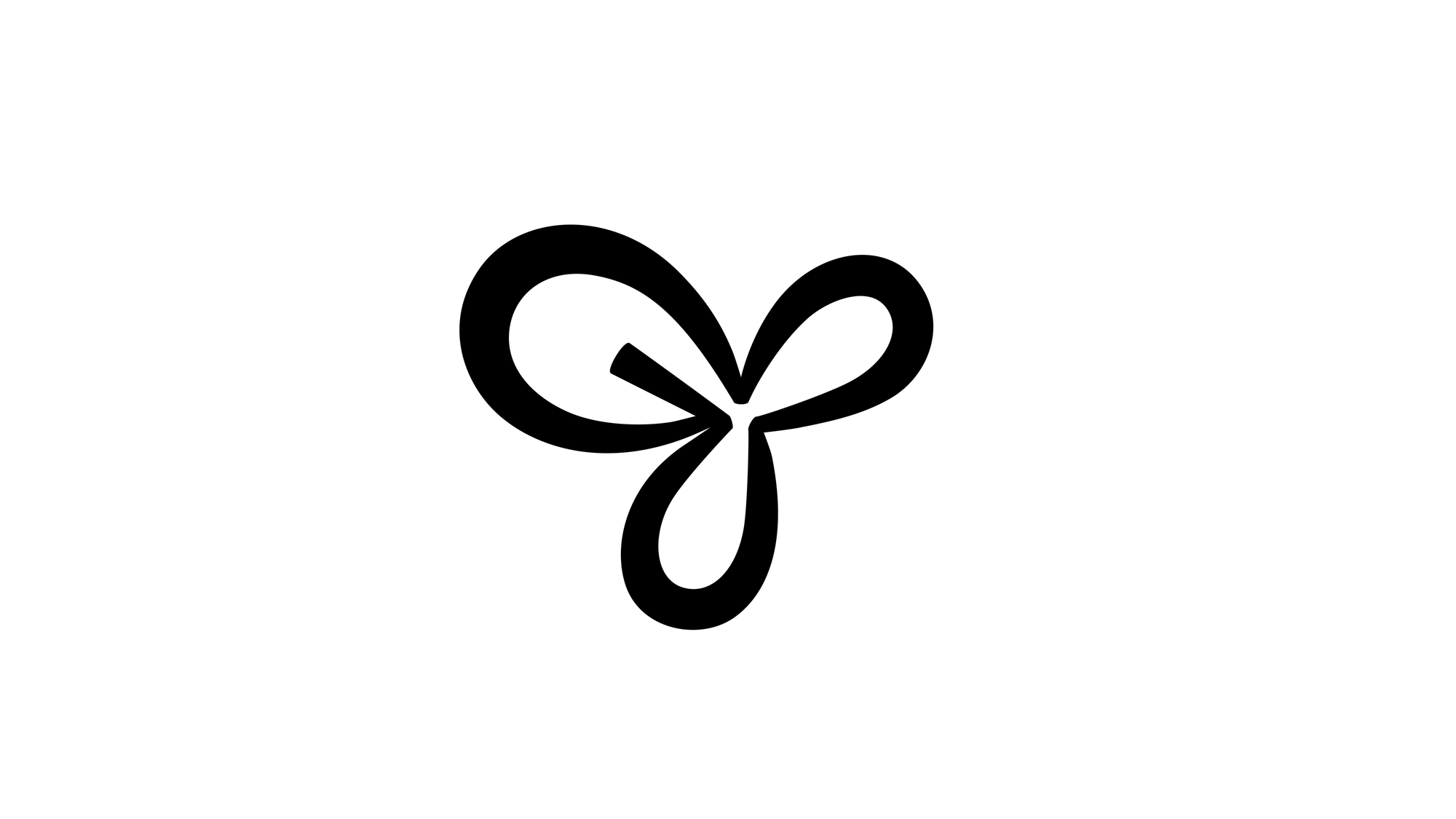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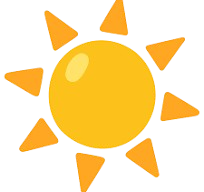





Discu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