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记者 | 60年代的社区遗产:生态村、太阳朋克与安那其
我第一次见到Erik是在线上会议上。
留长了头发之后,他没有几年前在中国照片上那样利落的形象,反而有点邋遢和颓废。
我第一次真实地见到Erik是在巴黎街头。
我们费力找到住宿的民宿之后,Erik已经在门口等我们多时,他穿着破洞的蓝色t恤,带着两大包行李和一把吉他,见到我之后,他从背后拿出吉他简单地弹了一首歌。
我第一次真实地见到自在的Erik是在Longomai。
他在社区大厅的钢琴前弹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松弛地和冠华对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
但无论哪一次,Erik都给人一种矛盾感:
他受过高等教育,却没有精英气质;他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却显得平和;他反对资本主义,却特别喜欢中国超市。
我把这种矛盾感归纳为许多类似的社区的共性:
他们游走于现代社会的边缘,想要创造另类,却又难逃现实。
Part 1:Longomai(龙谷脉)
踏出停在马赛的火车之后,似乎一下子走入了另一个不同的法国。因为地处地中海北部,加上大量的北非移民,马赛也被戏称为北非的首都。Erik带着我们在垃圾堆里穿行,说要在离开马赛去Longomai之前去拜访当地的一个“alternative space”。

在两侧的视线注视之中,我们拖着行李顺着石板路一路往下,途径马赛著名的Cours Julien街区时,墙面和地上的涂鸦都大量增加。据说这里是法国最大的街头艺术区,聚集了当地设计师、艺术家、旧货店、书商和漫画书店。
Videodrome是一个有多层的独立放映室,对面就是露天的酒吧区。这里不论周末还是平时都人满为患,像菜市场一样喧闹。我们来的这一天刚好放映室计划放映一部探讨亲密关系的影片,随映供应着空间自己diy的简易晚餐和啤酒。
除了Erik以外的一行人都有些局促,我们带着行李箱坐在人挤人的室外长桌上,盘子里是糊状的素食,Erik说相比于资本主义如意随形的巴黎,马赛的氛围让他感到更加亲近。
马赛的一晚是匆匆的一瞥,我们并没有真正得以了解这座城市,反而是得以更了解了Erik所喜欢的城市生活:替代性的,非主流话语中的城市。而我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做好了“进入Longomai”的准备。
在华人超市采购了足够多的菜品和调料之后,Eli开着他的小卡车接到了我们。从马赛一路北上,南法的路很少有平坦的告诉公路。两小时曲折的车程之后,又是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才远远看到位于半山腰的“Grange neav”。
#
我们去往的Grange neav(后文中,未加后缀的的Longomai均指Longomai网络中的这个Grange neav社区)是Longomai网络中最早也是最大的一个社区,位于普罗旺斯地区,其法文原意是“新农舍”。这个村庄最初确实是一个农舍,周边以产出石灰岩著称。这个村子和很多法国乃至中国的旧村庄一样,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走向了空心化,许多13世纪留存下来的石头房屋,被社区居民改造、维修、扩建后成为了现在的社区居住空间。

发源于1968年的Longomai社区网络,曾经的参与者主要是法国反文化运动中的学生。这场运动曾经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吸引了无数青年加入左翼行动和反主流文化实践。在70年代初,7个来自于不同背景的学生组织和一些有志于改变社会的学生在奥地利集合起来,希望一起出资做一个不同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实验。他们有的卖掉自己的房子,一同筹款,筹集到第一批购买土地的资金,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大省购买了一片土地,也就是现在的Longomai。七个学生领袖也因此称为了Longomai社区网络的七位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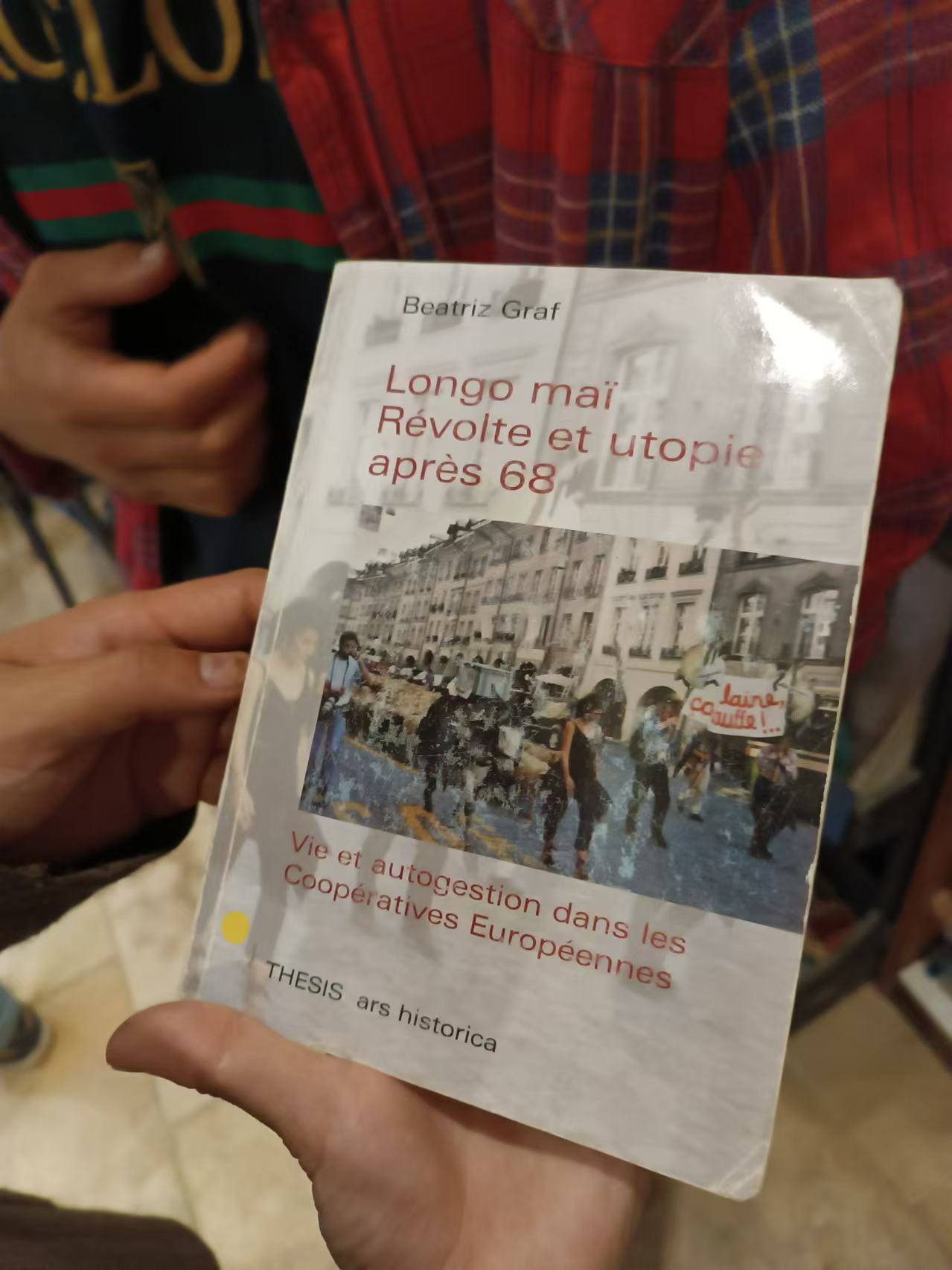
在普罗旺斯本地的方言中,Longomai的意思是一直持续存在的存在,他们用这个方言的意象创建了自己的社区名字,希望社区长期地存续下去。
这似乎一语成谶,虽然Longomai和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已经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再度回潮和历史的进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这个社区网络却得以保留、发展至今。
#
我们居住在一个具有嬉皮色彩的小屋子里,它也有自己的名字:Fatza。
依照Longomai的共识,一个人至少要在这里住满3个月才有可能提起加入社区的申请。在50多年的历史中,嬉皮们和具有DIY精神的背包客口口相传,从北美到南美再到欧洲,许多人在社区与公社中漫游,也因此又不少人来到这里,有的人因此一住就是数十年。
在停留的期间,为了方便自己也为了方便后来者,一群句有diy精神的旅居者建一所可以居住和短期停留的房子,这栋充满嬉皮士风格的夯土小楼“Fatza”由此诞生。
房间很暗,但并不显得阴森,皮质的沙发和毛毯随意地拜访在小小的客厅中。客厅的墙面随处可见法语的涂鸦和留下的文字,“让我们生活且创造”(Laisse nous vivre et creer),“嬉皮们,一起堆肥吧”(Les hippies, au compost)。以简单的木头搭起来的墙面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就和这里无数个不同的杯子和门口堆满的鞋架一样在提醒着你“这里有无数人留下的痕迹”。沿着一个不起眼的木梯,可以上到一个隐藏的二层,这里甚至还可以住下四个人,二层的小门推开是屋后的山坡,晚上上厕所的时候肉眼就可以看到银河。

厚厚的笔记本写满了往来之人留给Fatza的话。
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让你与过往的人连接起来的地方。
#
在Longomai,我们偶遇了手上纹有“道“和太极的Holand,年近70的Holand是最开始的7个创始人之一,每天,他会坐在社区大厅旁边的树下晒太阳、阅读和聊天。有趣的是,这7个创始人虽然都仍然在参与Longomai,但基本上没有住在同一个社区,Holand如今长居在哥斯达黎加的另一个Longomai社区,这次来到欧洲,也计划前往网络中的不同社区进行分享。
Longomai网络中目前共有11个社区,除了法国的3个和哥斯达黎加的1个,还有7个散落在欧洲其他不同地方,如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每个社区有不同的面向和特性,但他们共享着“反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哥斯达黎加的Longomai,他们为从尼加拉瓜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来的难民提供住宿和可以工作换取食物的农业合作社,也因此不仅仅是一个“社区”,同时成为了一个拥有700人口的农业合作社。
事实上,不仅仅是哥斯达黎加的社区,在Longomai各地,成员每天的劳动达到一定量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享有社区内的食物。在社区中居住的人,无论是居民还是志愿者,每天工作4、5个小时,上下午各自几个小时,其他时间可以不用工作,并且可以免费享有社区内的葡萄酒、面包等各种食品以及各类公共设施。因此,在社区中除了一定的工作时间以外,大部分时间可以看到人们围坐在树下闲聊与阅读,偶尔会有集体活动和外部分享交流。
公共物品接近于无限大,这是被他们称为“合作社”(Cooperative)的工作和组织方式。
#
在社区大厅的正门有一块平平无奇的木板,大家每天在这里更新社区内的情况、需要完成的工作以及做饭的安排,大部分日常的工作都是自发完成,重要或复杂的工作则通过会议进行讨论和安排。

这个大厅也是日常所有社区居民共同用餐和集会的地方,每天的午饭和晚饭会有人自动认领为全体居民做饭,而如果没有人做饭,社区食堂便不会开放,居民则需要自己做饭或寻找食物。
在社区自治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也非常自由。
大部分的“治理”发生在社区大会中,成员会在每周一的晚饭后共同讨论一些事先拟定的议题,每每有重要的问题发生(如房屋分配、新的修建项目),对应提出的小组会着急成员共同讨论,直到得到一致的结果。
虽然大部分是农业生产,但Longomai的成员实际上各自有着不同的工作类型。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以工作坊的形式参与到了将近十种不同的工作:制作果酱、蜂蜜、面包,管理电台、会议和文件……
Longomai已经实现了80%的生产自给率,大部分的食物、衣物和日常用品,他们可以自己生产,只有小部分无法生产但又不得不使用的消费品(比如沐浴露等)他们会从外界购买。购买的钱可能来自于个体,也可能来自于社区基金。
这个自从70年代便设立在瑞士的社区基金会至今仍然在运作,用来支持那20%无法自给自足生产的部分。在社区的专门劝募运作和专人管理之下,依靠着在运动中积累的关注和参与者,基金会每年都能收到总额不低的捐赠。
社区的所有劳动所得转化而成的现金收入,会汇入到这个社区基金会的各地社区子基金之中,而如果有合理的需要的支出,则经过各社区申请后使用。
#
Cedric是一位从来不自称无政府主义的安那其,也是法国乃至全欧洲的各种社会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对世界各地的行动的关注也让他一直在参与Zinzine的工作。
社区里有几十年历史的电台Zinzine,至今仍然在播报世界各地的公民行动和人权行动,他们以项目组的形式每周集会讨论内容,并定期把信息整理出版发往世界各地。在Longomai社区各地,只要认真寻找,都可以看到矗立在一座山头的电台发射台,从这里,信号传往南法各地,也通过互联网的形式传往世界各地。
某天饭后我们一起唱歌弹琴,唱到激动处,有朋友开始弹唱国际歌,从中文的独唱,到Cedric加入后的中法对唱,再到全场的中法合唱,仿佛在印证“革命老区”的国际地位。
有时候他会和我分享法国左翼彼此之间的吐槽,有时候他会关心当下年轻人的实践方式。他知道在当下以电台的形式分享信息已经不是主流,但他会坚持“他们那一代人的方式”。
他会对当下所谓“加密朋克”及世界各地的互联网行动感兴趣,并邀请说:如果你们想,我可以带你去看法国各地的安那其。
#
“社区”的操作方式、如何治理、如何对工作量进行计算,这些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恰恰是次要的。对他们更重要的是政治参与和行动,以及他们所持有的政治立场。在形成了前序的共识、长久的共居之后,具体多一分少一厘,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没有计算的必要。
在法国的实践中,他们并不会主动写下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方法,也不会关注社区的理论和经验,而是更多地发出声音、实现自己的政治心动。
“社区”只是作为政治行动的媒介,而并没有将其视为重要维度。这是我对法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观察。无论是龙谷脉还是其他事物,大家更多地将政治形而上的东西作为重要维度,而社区治理可能被放到次要位置。

但无论如何,在南法这片绿色与蓝色掩映的土地,“生活”才是第一位的。
Part 2:Traditional Dream Factory
在Longomai使用电脑,会让我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但在TDF,情况似乎不太一样。
决定去TDF源于朋友Nico,她在她的网站https://www.agartha.one/中分享了这个位于葡萄牙南部的新社区。刚好,TDF位于里斯本和tamera之间,我们因此有机会短暂地访问这里。实际地讲,由于我们到访时正处于葡萄牙的旱季,TDF本来就简单的建筑在荒凉的草地的映衬下,与其说是一个生态社区,不如说是一个废旧工厂。
但事实上,这正是TDF想要改变的。
TDF的创始人Sam曾经在美国工作,此后也服务过几家high-tech,期间以远程工作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漫游。但他不仅仅是在漫游中完成工作,在南非、美国和欧洲等地,他也在寻找一个可以实现他的想法——可以实现OASA理想的地方。
OASA是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实现他们的再生理想的线上社区,用他们的话说,是“A Web3-powered nature conservancy network serving regenerative human living spaces and the pla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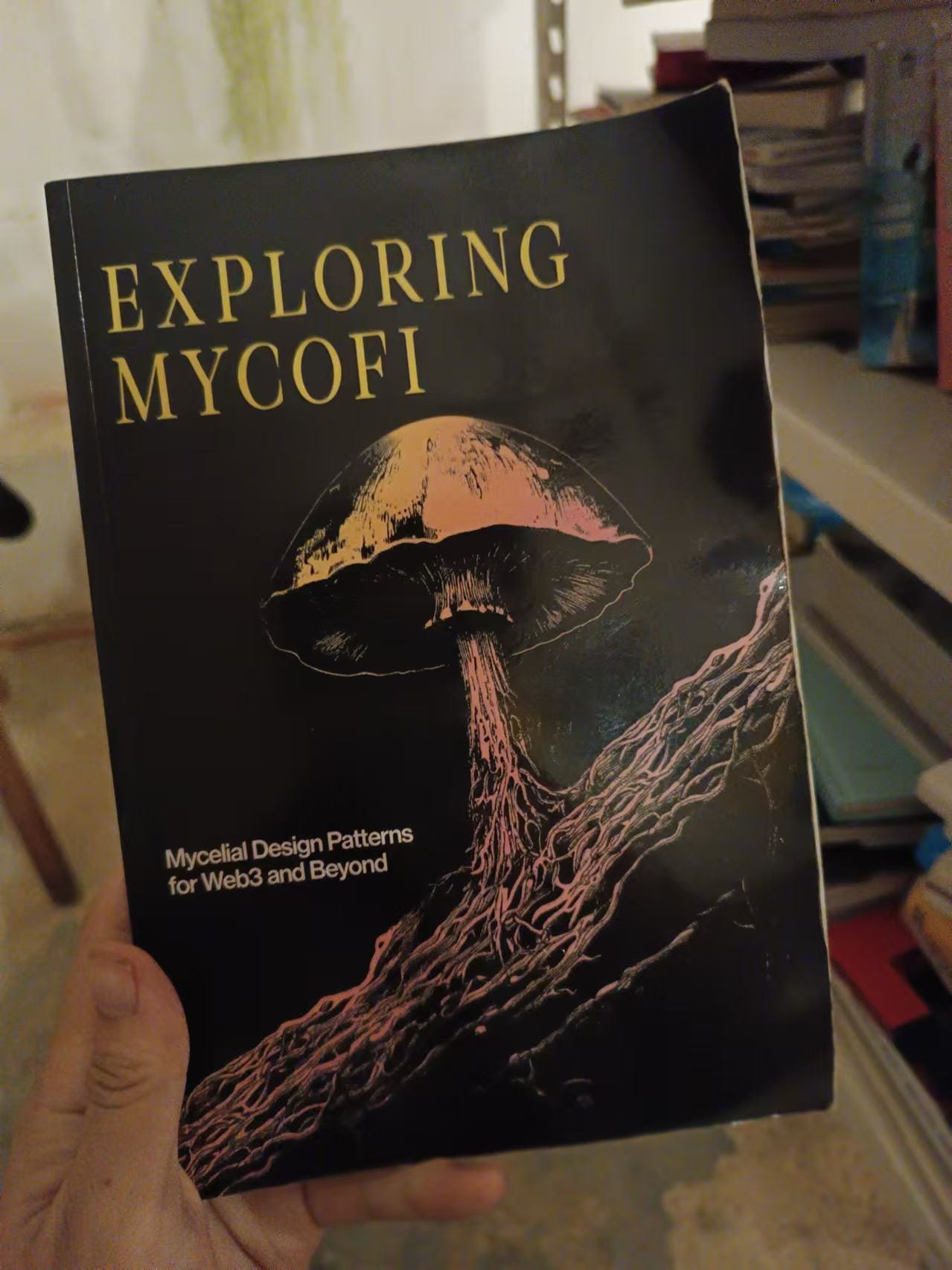
在OASA的白皮书中,你可以看到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菌丝网络(Mycorrhizal Network)和再生(Regenerative)愿景以一种完整的叙述被整合在一起。从一个可再生的愿景和区块链的技术出发,OASA描述了另一种可能的未来:反-反乌托邦(Anti-dystopia)的、太阳朋克(Solaropunk)的积极技术想象。
这里设想的不是一个赛博朋克的高技术低生活的未来,而是在技术驱动下更加人-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用Cedric的话来说,这似乎是“新一代的实践方式”。但在这些复杂堆叠的概念被具象和融合到一个具体的实验场所之前,没人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

Sam和OASA的朋友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承载他们这种实验的地方,并最终选择了葡萄牙。21世纪以来,葡萄牙在欧洲的地位很微妙,它越来越像是欧洲的云南或者大理。和云南相似,葡萄牙地处欧洲的西南部、远离传统的欧洲经济政治中心、自然环境优美且生活成本低。这些共享的因素似乎使得云南-葡萄牙-加州-中美洲和东南亚这些地区具有了一些相似的发展前景:一种Alternative发展的可能性。

TDF所在的地区曾经是小镇旁的养鸡场,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镇”周边主要的产业是养殖和农业。葡萄牙南部的土地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农业耕作已经变得地力匮乏,很多区域面临荒漠化,这个小镇也随着产业的衰落和环境的破坏而变得萧条。TDF抱着希望能改变这片土地的愿景而建立,希望通过可再生而不仅仅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使得这里重新变得充满生机。
在我们随着向导August进行社区tour的时候,他指着远方的另一个养殖厂:“对面的养殖厂经常会传来动物的哀嚎,在这边也可以听得到。我们看到那一个世界离我们如此近,就好似在提醒我们不能活在一个泡泡中,也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大部分是什么样的。”
在本地议员的支持下,Sam贷款买下了这片土地,并在三年前和朋友开始了在这里的实践。三年的时间并不长,没有长到能改变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的程度,但已经足够形成一个小生境。从最开始的几个人到如今的十多个人,许多长居和短居的人已经来到过这里,参与了这里的生活和实践。从一个养鸡场出发,这里逐渐开始生长出食物森林和各种各样的生态建筑(尽管他们的游泳池计划至今还是一个只有石头的大坑)。
我看到的是TDF居民的融入和平衡:他们发币,但并不让所谓量化治理困境来到线下;他们使用科技,但尊重人的生活节律和自然健康;他们吸取公社的经验,但不陷入脱离现代社会的悖论。
尽管这里脱胎于一个传统的工厂,但我相信它能变成许多梦想生长的土地。

Part 3:Tamera
Tamera存在于不同人的不同印象中:开放性关系、爱与和平、社会实验、生态保护、太阳能科技……在吉光片羽之中,很难有人在来到这里之前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什么是Tamera?

最早接触到Tamera,是在大理的社区中,一个朋友在闲聊时分享了他们最近在做的纪录片放映计划,片名叫The village of lovers,讲的正是Tamera社区的故事。
在大理错过放映之后,我又帮忙组织了在广州和其他城市的放映和推广,通过纪录片的一角,大家的印象是:一个过于美好的宣传片。后来,在全国组织《全新的我们》的放映中,在十个不同的社区案例之中,Tamera似乎又展示给我了另一面:生态的、自然的那一面。
它似乎不仅仅是要完成一个生活共同体的使命,似乎有想要更多在这个共同体中实验的东西:成为一个社会另一种可能性的样本。
起源
在德国,有一个至今仍在运作的著名生态社区实验——ZEGG。90年代,最初被称为"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或"社会与文化实验基地"。在席卷全欧洲的68年后的反文化思潮之后,一批从70年代就开始进行各种社会实验的人怀揣理想的实践者最终来到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探索。
但显然,这批人并不拥有完全一致的理念。在Dieter Duhm、Sabine Lichtenfels两位成员的领导下,一群德国人带着“在哪里创造一个地方来创立全球治愈生物群落项目”的理念来到葡萄牙,创立了如今被称为tamera的社会实验。

Dieter Duhm是一位社会学学者,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思考曾经影响了无数德国人,而Sabine Lichtenfels则对灵性探索和与万物沟通有着独特的天赋。在他们的领导下,Tamera形成了独特的气质。据说,一个社会活动家来到这里会开始探索灵性,而一个灵性探索者来到这里会开始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看起来风景优美的Tamera,在30多年前还是一片荒漠。由于长期的过度耕作,葡萄牙南部普遍面临着严重的土地退化和沙漠化问题。这群实践者用三十年的时间将这里变成了一片绿洲。
Tamera认为,地球上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创造我们的世界(自然世界),另一个是我们创造的世界(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现代城市文明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从自然系统中脱离,形成了一个独立运转的体系,并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改造。

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恐惧,这种恐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以匮乏为前提,以竞争为手段,让人们陷入压抑和不幸的状态。人的主动性被限制,更多地被嵌入到既定的工业体系中。
面对这种情况,Tamera试图创造一个"治愈生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开辟一个另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探索着一套能够自我运转的非资本主义体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核心是构建以爱和信任为基础的新文明形态。
为什么是爱?
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家庭是我们最难以被观测到的存在。
家庭作为私人生活的领域和场所,人很难将自己的目光投入到别人的家庭中。因此所有的私密场所和隐秘地带都为资本主义体系和父权社会提供了非常好的运作场域。只要他控制了这两个家庭,基本很难撼动这个体系。因此家庭实际上是我们最初所说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它是整个体系的核心。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即瓦解或者改变家庭结构。因为人对家庭的需求、占有欲以及当前核心家庭的一对一关系并非自然产生,而是与人的文化建构有很大关系。
如果我们能解放一对一关系,人们就可以在社区中相爱,在团体中彼此支持,并且不再局限于一对一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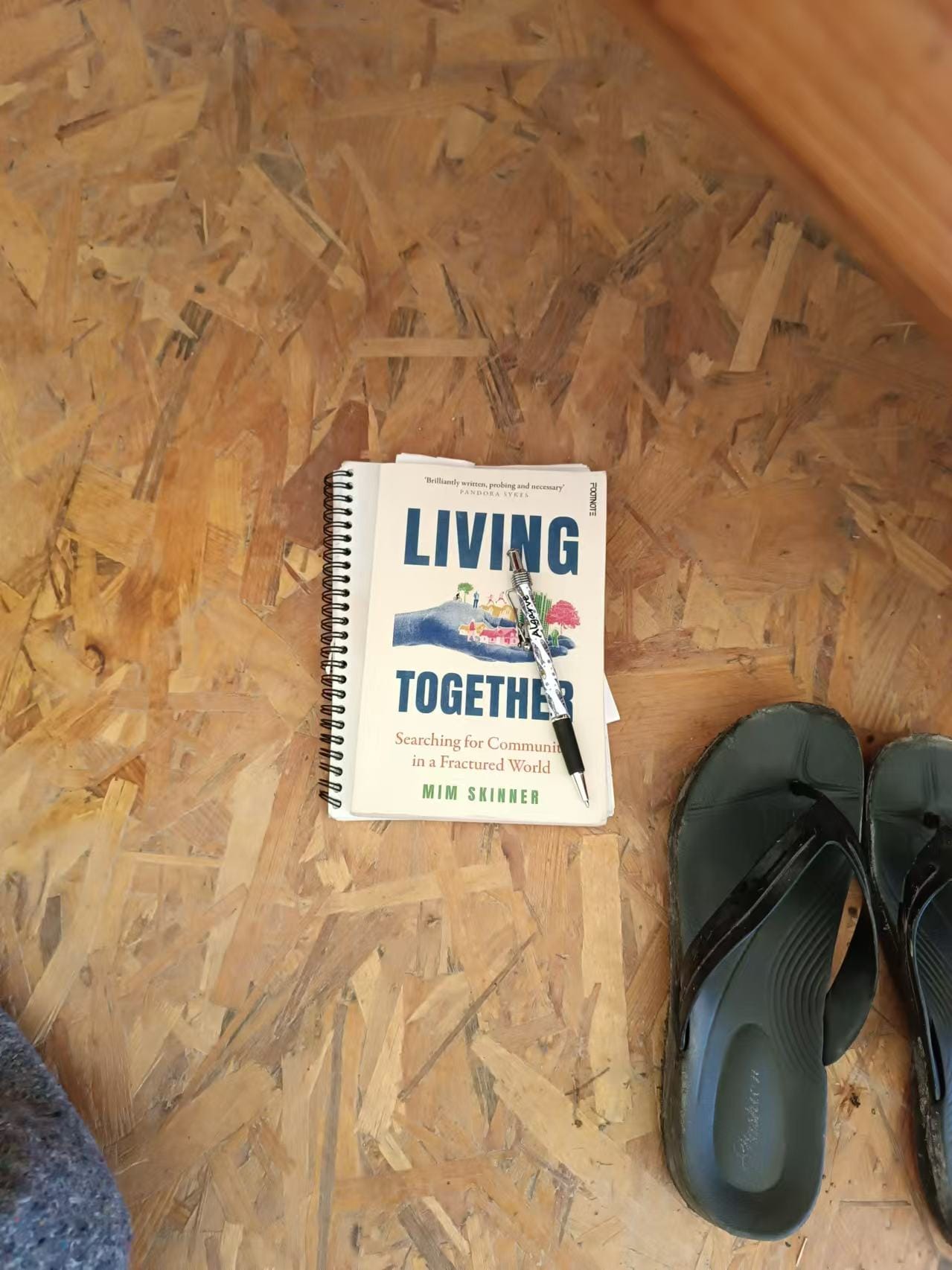
他认为这样人可以从狭隘的人格中走出来,从害怕失去和害怕人的离开中走出来。如果我们能改变家庭关系,很可能将人从恐惧体系中解放出来,构建出以爱和和平为核心的社会体系
为什么是灵性
在Tamera,有一个每一个访问者都希望访问,但又保持敬畏的地方:石圈。
石圈由96个不同的石头组成。根据特殊位置进行拜访,每一个石头上都有着不同的符号。据说这个阵形可以让人在这里更好地感悟更高层的能量,或者感受到能量的流动。
老实说,我是一个很不灵性的人。早上来这里参加“力量之环”的晨间冥想,除了被淋了一身的雨,似乎没有什么高维能量影响了我。
我愿意尊重,但也很好奇,在我看到的那些具有长久延续性的共同体中,似乎都走向了对某种价值、共识甚至对象的信念,一部分抽象化为了一种信仰。这真的是每一个共同体的宿命么?
理念
Tamera并不是生产型社区,它不像其他公社后续发展状态,而是更多地偏向自给自足,依靠外在捐赠、课程内容施加影响力等方式获取基本所需的支出。他提到社区内部没有产生交易,也没有收取货币。虽然同样遵循接近共产的方式,但他们允许社区成员在外工作,也依靠着外界访问者来获取课程收入和捐赠。
他们希望在全球各地支持了不少其他类似行动小组或者组织进行类似的和平爱研究和学校,也会通过联合国等其他平台施加自己对外的影响力。
因此,他们虽然关注日常生活并以此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实践和表达,但正是这种表达也部分异化了他们的生活。在和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有不少成员表达了对开放关系理念的不满,也有很多新加入的居民对由年老一代把持的社区理念和治理感到不满。

而这类矛盾似乎也在许许多多的其他生态村发生。在我们访问的时候,来自欧洲最古老的Findhorn生态村的一位老居民也来到了这里,并分享了他的故事。似乎这些曾经由嬉皮士、另类生活探索者、灵修者和政治异见者组成的社区都在面临相似的那些困境。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活下去?又如何能继续邀请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运动?如何真正影响主流社会而不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
他们还在寻找答案,而或许我们也是。
Uncomments
人们为何迷恋“附近“?在一代人体验过脱离共同生活的孤独感之后,几颗豆子脱离了豆荚。它们生出根茎、枝叶攀援而上,主观或被动地牵引着其他植株去向沃土,更早地成熟。巨构和森林无法仔细地照料每个角落。我越来越感到,向土地、或某种能够将群落团结起来的东西伸出双手,令肉身与灵魂得到滋养,几乎是每种社会实验的根砥。那既是Alexis在文中描绘的”生态村“与太阳朋克实践,更是我们探索族群、国家与社会存在方式的那喀索斯之影。
在加密世界,我们看到数字游民在全球 Pop-up City 之间游牧、Network State 领袖签约未来的国土、Vitalik 在博客中写下未来城市的愿景:在进一步数字化的历史趋势中,向基于加密的去中心化与隐私保护迈进,向经济学为底层的协议治理迈进。
回看人类的历史,寻找一片土地,孵化独特的文化迷因的冲动早已融入我们的骨髓。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记录了探访欧洲一系列共识社区的体验。与加密思潮中关注现实与技术的耦合不同,这些社区中的伙伴更加热衷于无限的艺术与表达、自给自足的共产生活、生态保护、爱与和平、关系开放与灵性整合.......
站在今天看来,这些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激进、早已在话语体系中被探讨与演绎。然而当我们回到上世纪 60、90 年代、这些社区刚刚诞生的日子,或许会感受到与今天加密世界尝试创造新范式一样的叛逆。
然而,倘若没有暴富的期许,多少人愿意生活在加密国度?穿梭在 pop-up city,许多人与我一样在寻找着发展的机遇,试图从流动性掠夺筹码。
跟随作者的脚步感受这些生态社区,我看见人们寻觅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回归土地,安居乐业, 逍遥自得。我想我随时可以加入他们,但就是有一份不甘。
同样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我们,想要创造新世界,却又下不了市场的赌桌。
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Discussion